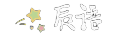暂无AI摘要
暂无AI摘要 昨天我妈告诉我,趁着难得有的两天阴天,已经把家里的四五亩玉米收了。是用收割机收的。村里大部分的玉米也都已收或者正在收了。她是跟我打视频说的,是在问完我生活及工作的情况之后,临近挂电话时才补充说的。我妈的语气很平淡,似乎是在聊去年的事情。
玉米秋收情况的文章消失了以后,我妈宽慰我说,这不奇怪,她知道是什么原因。我让她细说。她说肯定是你写的太无聊了,你写亩产多少多少,斤价多少多少,这些数字谁看了不觉得无聊?这谁不知道啊,干活的种地的都知道。再说了,咱自己知道就行了,你偏偏想写出来让那些不干活不种地的人知道知道,那这不怨你怨谁?我说是。我妈继续说,你这样,你下次再写这类文章,你多谈谈你干活的感受,其他的东西你少写点就中(行)了。

、
我妈说的是对的,有些方面她没有明说,我也明白她的意思。我想,大家也明白她的意思。许多时候,一个人,或者说一部分人司空见惯的事情,就不要让其他人都知道了。你若是非要当这面镜子,那么焦点就从“事情是否合理”变成了“你是否该说”。相较于关注前者的解决,解决后者明显更容易些。所以,平淡即可,如果你不能平淡,说明你经历的事情还是不够多,你还是比较幸运的。
我写文章有一个很明确的立足点,就是“人”,写事不在于事,我更在乎事情对人的影响,在乎人的感受,根本还是在于“人”。我并非就喜欢那样冷冰冰的数据铺垫,只是没有那些,就无法去表现人,无法去描绘人的某种状态产生的原因。大概是我的性格,或接受的家庭教育的原因,每次在田地里干活的时候,我的触动都是非常大的。说句不怕叔伯姨姆骂我的话,有时候干活时,我不是因为技术不熟练而干的慢,而是我的注意力都在他们身上,而并非眼前的玉米或花生上。注意力在人不在事,自然就干的慢了。
我注意到,农村的干活的人,不管是如我父母般五十出头的农民,还是六七十岁的老年农民,随着年岁的增长,他们的眼睛变得越来越黑了。我说的“黑”就是客观描写,就是他们眼珠的黑色部分占卜变大,眼白减少。原本的眼白部分或是被眼黑所挤占,或是代之以浑浊的昏黄色。我在城市里观察过上了岁数的人,他们的眼睛,没有给我这样的感觉。

再加上他们眼角及额头的皱纹,不,不能说是皱纹,那是一种沟壑,像是嵌上去的。这种沟壑与那越来越黑的眼睛是一体的,让你不敢直视他们的眼睛。不过他们好像洞穿了你的心思似的,他们在干活之余或休息间暇看你的时候,或者对着你说话的时候,往往都是伴之以笑容的,他们是以笑示人的,这让你不再害怕那种黑色及沟壑。他们用笑帮你克服了这一点,你也就自然能与他们谈说自如了。
关于那种不敢直视的敬畏,在谈笑风生的时候你不会有这种感觉,埋头掰玉米干活的时候你也不会有这种感觉,因为这时候你在他们看来是学生或是孩子,他们是劳动人民,你面对他们只有“敬”而不会有“畏”。怕就怕干的时间久了,他们不再把你当成一个干活的外人了,他们恢复常规的劳动中的自然了,四周突然静下来了,除了劳动的声音其余的都没有了,这时候你再看着他们,那种眼睛的黑色与眼角的沟壑带来的“畏”就陡然压上来了。
一个话题结束,一旦静下来,他们的表情一旦凝滞,或者说他们正在干着活,但突然停下来了,站着想着一些什么事情,或是挽一挽裤腿坐下来了,然后看着远处发愣。你这时候就会有一种强烈的震动,他们想到了什么呢?这样的秋收在他们的一生中已是很多次了,即使下着雨手掰着玉米,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困难事儿,农业生产是脆弱的,种地干活所带来的是一种惯例感,只不过,外人把这种惯例感叫作疲惫罢了。
他们从年轻到现在,半个世纪的光景,他们经历了太多的事情:有关农业生产,有关土地性质,有关劳力工分,有关粮票公粮,等等等等,太多太多了。他们或仍然是家庭的顶梁柱,或仍然想为子女分担些生活压力,顶梁顶梁,或是浇地或是掰玉米或是薅花生或是栽辣椒或是打烟叶,这都是“顶”的一种方式。而你的“畏”,就来自于此。
你把那些在田间干活的、爷爷奶奶或叔伯姨姆的一生纵向了解了去看,你一定会有这种“畏”的。这正是他们眼睛越来越黑,沟壑越来越深的原因,也是你不敢直视的原因。你不敢直视,是因为你已经具象地见到了继而意识到了劳动二字背后的沉重。太沉重了。因为沉重,所以扛起这种沉重的人们,都配得上万岁二字。
我在10月14日晚的B站直播时,谈及到了这一点,我禁不住泪流满面。这是我在雨中和农民一起掰玉米或薅花生时的真实感受,也是我之前从未有过的。当然我也清楚,要想通过简单的劳动就做到感同身受,那是不可能的,我只能尽力做到和他们保持同样的视角,我只有理解了那越来越黑的眼睛,才能尽可能去和他们保持一致的视角,有了这样的视角,我再去看待田地与作物,再去通过文字记录一些情况,才是最宝贵的。宝贵的不在于记录的事,而在于人。
历史是由人创造的,立足于人,理解了人,才能去理解人所做的事。经历的越多,理解的越多,总有一天,我们也会有那越来越黑的眼睛的——我们是柱,早晚也得把梁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