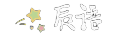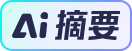 暂无AI摘要
暂无AI摘要 过去一年,我曾经数次关注普通打工人的权益,在我为普通人争取权益的时候,总有一大批人来问我,出了劳动纠纷,员工可以自己走仲裁,你在这里煽动舆论,是渲染劳动仲裁难度,实在是居心叵测。
2024年8月,工人日报曾做过《仲裁维权经历不该成为就业“绊脚石”》这样一篇系列报道,《工人日报》记者通过三篇调查发现:
一些劳动者的劳动仲裁维权经历,会影响其后续求职,甚至被拒绝录用。现行法律采取罗列加兜底的方式,暂时没有把和其他用人单位有仲裁或诉讼的情况加入其中。
《工人日报》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报,是中央主要新闻单位之一,我不知道这种报道属不属于渲染劳动仲裁维权难度,煽动舆论,居心叵测的范围。
爱法援的猫头鹰也在过去的一年积极投身一线劳动仲裁,我们来不妨听一听这一年,他在基层法律工作中得到的认识。
一、情况概述(案件数量以及基本情况)
裁判文书网上很难找到劳动仲裁记录不予录用的相关案子,并不是因为这类事情不常见,而是因为很少有企业会直接以劳动者存在劳动仲裁记录为由,书面拒绝劳动者入职,所以很少有机会进行起诉。而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也以调解或者驳回起诉进行处理,这类案件具有一定争议性,一般法院并不希望这种争议性案件入网。
二、就现有法律对该问题的规制来看,可以说是基本不存在规制。
《就业促进法》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视。”同时,该法第六十二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实施就业歧视的,劳动者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乍一看似乎赋予劳动者诉权,但是实际上从该法立法目的来看,该法主要是为了保护由于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的劳动者的就业权利。而将是否具有劳动仲裁记录归为第三条的“等”字明显属于扩张解释,对于该扩张解释是否能够适用于该法,取决于人民法院的理解。这是从《就业促进法》角度入手进行维护的困难。
从《个人信息保护法》而言,情况似乎更为糟糕,该法在一定情况下赋予了用人单位以订立劳动合同的需要为理由要求劳动者提供个人信息进行调查,这是完全合法的
由于只要劳动者“形式上”同意用人单位搜集获取劳动者个人信息,用人单位就获得相应权利,因此用人单位完全可以借助我国用工市场你不干,有的是人干的生态,滥用市场优势地位要求劳动者签订《同意书》。这种公权力在劳动领域的缺位很大程度上将会使劳动者的权益受到损失。
大多数情况下,存在背景调查制度的用人单位会在发放Offer前对劳动者进行背景调查,一旦其调查出劳动者存在劳动仲裁记录,就可以直接以其他理由拒绝发放offer,这种情况基本上就规避了任何法律的限制,因为用人单位并不是以“劳动者存在劳动争议”为由拒绝发放offer,属于“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因此也不能主张任何责任,政府以及法院不能对此进行干预。 所以劳动者面临的实际情况是:甚至不知道以什么理由起诉用人单位,根本不存在抓手。
我们认为解决目前情况的办法是有限的,核心问题依然是,背调本身并不违法。因此至于下一家用人单位到底从上一家用人单位获得了多少关于劳动者的信息以及这些信息是否客观、准确,是否影响了劳动者的入职我们都无从得知,规制就更无从谈起。
换言之,如果现行法律不能明确和劳动者站在一起,不代表公权力对企业所谓经营自主权进行明确的限制,而是继续选择走中间路线,既要维护企业合法权利,又要保障劳动者合法权利,那么就一定存在一个矛盾的空间,而在这个空间里就是用人单位可以滥用市场优势地位,与其他用人单位进行勾结串联进而损害劳动者合法权利。
这还是在上海这种司法透明度相对更高的地区实践得到的经验,我们也就能了解到劳动仲裁的现状了。
无独有偶,去年年底。三联生活周刊曾经报道过类似事件,详细采访了几个因劳动仲裁经历而失去工作的年轻人。报道指出,目前背景调查除了行业内部人力资源管理者形成联盟,互通有无之外,也已经形成产业链,除了应当核实的学历工作经历的内容以外,重要的还有一项劳动仲裁等诉讼记录。
其他相关的困难还包括劳动仲裁的解决要靠司法判决,目前仍然相对漫长,成本完全由个人承担。劳动者的仲裁记录和其他数据捆绑贩卖,而购买者往往是资本结盟的企业主。当法律赋予的权利已经异化为“职场案底”,所谓“依法维权”不就是西西弗斯推石头,推上去,也免不了整体滑向坡底的命运。
你说法律我都觉得有点好笑
所以现在我们再回头看看,有些人所主张的劳动者要拿起自己的权利为自己维权,这当然是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但问题是,这些人在支持劳动者拿起武器为自己维权的时候,往往会认为要求改善劳动环境的言论是在添乱,是在推塔,是巨婴自己不想斗争,把责任推给政府。
一个合格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学习过两点论和重点论之间的关系,对于劳工权益的问题上也是如此,我们既要普法,支持基于个人的仲裁,又要促进劳动监察的进步,并且劳动监察的进步一定是重点。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真照有些人说的那样,要指望打工人做自己劳动关系的第一负责人,强调劳动仲裁作为准司法环节的作用,实际上是说,最后一道防线应该最经常被用来组织防御。那我可就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问问这些朋友,前面的防线为什么频频被突破了。
更进一步说,当资本通过舆论污名化构建起多重防御工事时,个体的“依法抗争”注定是孤立无援的散兵游勇。
政治有这样一道考题:资产阶级宣扬“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此,法国学者阿托尔•佛朗斯说:“法律以其庄严的平等,禁止穷人也同样禁止富人在桥下睡觉、沿街乞讨和偷面包。”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指出了这种平等的本质:
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进行的,这里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但马克思并不是在歌颂劳动力买卖带来的人造天国,而是进一步阐明,这种表面上的自由其实是不自由的根源:
一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就会看到,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象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
“权利存在”不等于“权利可及”,揭露劳动仲裁当中的隐性门槛和代价,恰恰是帮助法律落地而非否定法律。
你不能只在对外的时候讲你死我活的国际斗争,对内就要打工人自己来做自己权益的第一责任人,这种观念上比户晨风还要更自由市场化,更右翼,本质上是完全的资产阶级论调。这种人也能顶着脑袋装出一副左翼的面孔,完全是一种政治话语的失调。
一定会有人说你们这帮王佐,要求的无非是地上天国,是要求国家党和政府给你做好一切工作,自己享受成果。
我劝大家还是不要这样想,哪怕从最功利的资本主义社会理论上讲,劳动者交了税,自然有权要求国家保护自己的权益,通过代表呼吁立法。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说,为人民服务这几个大字还写在中南海的影背上呢,我们的国家还没有丢掉70年前的全部遗产。
今日某些人将劳动仲裁塑造成“天赋人权”的神话,却刻意忽略神话背后的代价:当工人被迫用未来的失业风险赌现在的判决,用职业生涯兑换一纸胜诉裁决时,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剥削呢?
真正的解放从来不是让无产阶级在既有规则下孤军奋战,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长期以来是国民党政府保卫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口号。从马克思到毛泽东,左翼从来都不会停止对规则本身的审视。
如果你真的在乎无产阶级权益,如果你真的在乎社会主义的原则,结论不一定是国家全面插手企业事务,但至少应该支持国家落实劳动监察服务。
如果某个群体既不关心中国社会的变化,也不关心中国人民的死活,让他还关心什么内容根本就不重要。
谁一而再再而三的忽悠你公平正义要自己争取、指出出路在劳动仲裁,把指出劳动场域存在的现实问题当场推塔造反的,有一个算一个,都是资产阶级的走狗。
有些人提出问题,是为了问题的解决。有些人反对提出问题,是为了怕别人看出来,自己恰恰就是问题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