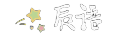暂无AI摘要
暂无AI摘要 法归于一人之手,君主凌驾于法律之上,“以法治国”成为当权者施行专制独裁统治的工具而大行其道。
韩非在《饰邪》中说,“先王以道为常,以法为本”,而在《有度》中得出结论就是:“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
“以法治国”本无可厚非,甚至可以看成是一个超越时空的伟大远见,毕竟韩非“以法治国”思想比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足足早了1900多年。
但是,孟德斯鸠提出的是“权力的分立”,以防止自由政体滑向专制政体。而法家的法治,却不是民主的法治,而是十足的专制主义法治。无论其怎么鼓吹法治的公正“不阿贵”,宣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一个不容辩驳的事实是,法家的“法”却在君主面前望而却步:
不是法治约束君主,而是君主独揽法权;不是法大于君主,而是君主超乎法之上。
法家,就是把君权绝对化,君主享有唯一的、绝对的权力。为了使君主的神圣权力不受侵犯,韩非主张尊君卑臣,并提出要“强公室,杜私门”,主张对那些私门势力和好比恶虎一样的权臣,要散其党收其余,闭其门,夺其辅,予以坚决铲除和镇压。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是怎样穿上“以法治国”的外衣而让独裁专制大行其道的呢?
我们可以从法家为专制君王贡献的那套“法治”理论中找到根由。韩非总结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的思想,提出法、术、势相结合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理论。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商鞅重法是要健全法制,万事以法为先;慎到重势指君主要独掌军政大权,树立君王的绝对权威;申不害的重术则指掌握政权、推行法令、驾御群臣要有策略和手段。
韩非推崇商鞅的“法”和申不害的“术”,但他又认为申商各自的学说都有缺点,首先是没有把“法”与“术”结合起来,其次是“未尽”,所谓“申子未尽于术,商君未尽于法”。
韩非认为,国家图治,君主要善用权术,同时臣下必须遵法,这就是“术”与“法”的结合。
与申不害“术”的策略不同,韩非的“术”主要在“术以知奸”。他认为,国君对臣下,不能太信任,还要“审合刑名”,从另一面而言,这实际上就是君主的“奸诈之术”。
在法的方面,韩非特别强调了“以刑止刑”思想,强调“严刑” “重罚”。
那么,怎样才能保证君王能够推行“严刑” “重罚”呢?
那就需要“势”了,所以韩非就认为光有法和术还不行,必须有“势”做保证。“势”,即权势,政权,就是君主的权力和地位。所以,韩非又赞赏慎到所说的“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提出了“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
韩非强调术,是要君王用术防奸,以避免大权旁落;同时强调要有统一的法,术是为法服务,没有统一的法,就没有统一的准绳,术的使用就失去了方向;还要强调势,不是人与势的结合,而是法与势的结合,也即强调的不是人治而是法治。
法、术、势之间,本应构成“法与术”“法与势”“势与术”这三种关系,而韩非却只提及两种关系,即:“法与术”和“法与势”。为什么唯独没有“势与术”的关系呢?
这只能说明韩非是以“法”为核心构成与术、势的关系。韩非固然指责商鞅忽略术,但是,在他看来术只是保证法顺利推行的手段;韩非固然肯定慎到对势的重视,但是,他指出势必须与法结合,不与法结合的势,不如无势;韩非批评申不害面临新旧法“相反”“相悖”的局面而“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仍然是强调法,只是区别旧法与新法。
没有“法”的存在,“势”与“术”无论怎样精妙,都是扯淡,都玩不转。法是主体,是内容,是方向,是政治性质的规定性,在法、术、势系列中,法是核心。
韩非的这套“法、术、势”结合的理论来源于何种思想,而目的又是去向何方呢?
韩非是支持“性恶论”的,与儒家“人之初性本善”相反,法家认为“人性恶”,人生在世都是为了私利,而且这种追求私利的思想不为亲疏好恶所左右。所以,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不能靠道德说教解决,君王不应指望以德治理天下,所谓慈爱出忤逆,“母不能以爱存家,君安能以爱持国?”
因为“人性恶”,所以就要“以恶制恶,以暴制暴”,这就是韩非的“暴力论”。法家认为赏罚是治理天下的“二柄”,但对这“二柄”的使用有所侧重,要“重刑少赏”,要人自觉地改恶从善是不可能的,如同“恃自直之箭”“恃自圜之木”一样的不可能,所以,只有外力强制。有效地制止人犯罪的手段,不是赏赐而是刑罚。
韩非从“性恶论”出发,到“暴力论”却并未而止,却是进而归于“独裁论”。因为,人性恶,所以要用暴力对付,而暴力唯有掌在君王手中,因此自然是独裁论为核心。
韩非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所谓“圣人”,乃最高当权者,“要”指的是“法”。“圣人执要”就是指最高当权者要牢牢独揽“法”之大权,按照法度对臣民实行赏罚的同时,要独握赏罚“二柄”而“自用”,不假予任何人。
法、术、势,性恶论、暴力论、独裁论,这两个系列的结合,便形成韩非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理论的实质,那就是“君主享有绝对的权力”。
显然,法家的法治思想相对于民主法治来说,相去甚远,甚至对于专制法治来说也并不算完备。虽然法家明确提出了“法不阿贵”,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但这可能也仅仅比儒家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多维护了点法律的尊严而已。
法由谁来制定?按照什么程序制定?都被韩非忽略了,只是一味强调君主“独执法要”。这就必然将立法权、执法权都集中于君主一人。这样的君主对臣民自然握有一切生杀予夺之权。法管不了他,而他高于法、大于法,他就是法的化身。
君王不受“法”的约束,便无法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样的当权者无疑是专制主义的独裁者,“以法治国”也便成为其施行专制独裁统治的工具。
王在法下,私有财产和人身自由不可侵犯。美西方早就有了这《大宪章》约束,进而发展成引领世界潮流的自由世界。
自由民主博爱,对接对岸,大中华民国全恢复,热情拥抱世界,为真正反霸反独裁反法西斯的,才是我们重新焕发光辉活力唯一之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