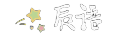暂无AI摘要
暂无AI摘要 1
长时期以来,每当看到“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之类的语句,我都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就好像身体的某个部位被叮咬了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无论我自己的亲身经历还是从社会上看到的大量事实,所谓“不要让”之类不过是人们制造的噱头而已,在改变孩子的命运问题上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事实上,绝大多输了的孩子就输在起跑线上,甚至输在距离起跑线很远的娘胎里,这几乎是不可逆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广泛流传着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以及“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天生会打洞”的俚语,就真切地描述了这种情形。有鉴于此,我曾经写《血统论是有道理的》一文,指证并辨析了隐藏在我们社会深处的某种机理,揭橥了大多数人实际上所处的社会位置。
“某种机理”是什么机理呢?实际上就是社会公平还是不公平的机理。血统论当然是典型的不公平的机理,这种机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曾经达到顶点,成为一部分特权阶层家庭子女的精神支撑。我这里之所以用“精神支撑”四个字,是因为当时的社会情绪普遍比较激昂,具有表面化的特点,而真正潜行于社会运行深层的小部分人大量占有政治、经济、文化资源问题,并没有被注意到,更不要说被清算了。换一句话说,历史无论当时还是以后,都没有为人们提供深刻思索和改变这种状况的条件。血统论横行的年代,人们还以为那只是一些年幼无知的孩子们的吵吵闹闹,没有将其上升为社会本性的反映的高度。只有极个别思想先行者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极端严重性,于是有了遇罗克的《出身论》,全面分析和批判了产生血统论的文化土壤,即其存在的历史与现实的原因,结果遇罗克被杀掉了。遇罗克之所以被杀掉,我认为不是因为什么别的东西,就是因为他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错误”地指出了这个淤积起来的社会症结,或者说,触碰到了社会最要命的病灶,结果被触碰到的“病灶”感觉到疼痛,于是痛下杀手了。
杀了遇罗克以后,“病灶”是不是就消失了呢?显然是没有,它只是不再疼痛了而已,这意味着它可以在民众的普遍麻木中继续惬意地存活下去了。是的,随着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血统论”在表面上当然是没有了市场,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寄生在社会机体内部的毒菌消失了,实际上毒菌所产生的病灶还在,还在不断对社会肌体的健康造成影响,也正是因为这种影响,长时期以来,学界都小心谨慎地躲避着关于血统论的话题,血统论无论在观念层面作为社会机理,还是在实践层面作为社会运行样态,都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理和遏制,它仍然发挥着作用,并在相当的程度上造成了本文标题所示“堵塞社会上升通道”的消极社会后果。
只要你没有丧失对于现实的感觉,你就一定能够发现,截至目前为止,“爹”在人们的命运状态中,仍然起着至关重要甚至是无可替代的作用,这种作用远远不是不具备“爹”的条件的人通过宵衣旰食、夙兴夜寐的努力就可以抵消得了的——这句话的另一个意思是,如果你出身寒门,比如说你是工人后代、农民后代、下岗工人后代、农民工后代、小商小贩后代,无论你怎么奋斗,你最终都将无法拥有“官二代”、“官三代”以至于“无穷代”所拥有的政治、经济资源,那些拥有这些资源的人合情合理地形成了垄断,他们合情合理地在政治上站得了先机,成为了像他爹那样的权力者;他们合情合理地在经济上成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受益者,有的已经裘马轻肥、重裀列鼎、富可敌国……甚至可以说,他们出生的时候就被政治、经济的锦被包裹着,即使他们不愿意,也不太可能走入他们命运的反面。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起点的不公平”。“起点不公平”很大程度将决定遭遇不公平一方的整个人生都处在不公平状态,所谓“社会缺乏公平正义”,所谓大面积的“阶层固化”,说的就是这件事情。
2
今天我想着重指证的,是另一层社会状况,那就是各行各业大量存在着的“近亲繁殖”现象。
“近亲繁殖”现象和“血统论”有一定的关系,但它还不是“血统论”本身。如上所述,“血统论”的危害主要来源于“血统高贵”的人对“血统不高贵”的人的社会空间的排挤和社会资源的垄断,这种与社会公平正义背道而驰的排挤和垄断,在任何社会形态中都普遍存在——资本主义社会来得更残酷更血腥——它甚至成为了社会通则,人们深恶痛绝的“赢者通吃”、“近水楼台先得月”从来没有被完全禁绝;“马太效应”始终都在发挥着效应(“马太效应”源于《圣经·新约·马太福音》里的一则寓言:“凡有的,还要加倍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与此相对照,“近亲繁殖”现象则带有更典型的权力社会的体制性、制度性特点,也就是说,没有一定的体制、制度保证,或者说没有体制、制度性缺陷,“近亲繁殖”是很难“繁殖”起来的——这样看来,问题显然比较严重了。
我不是随便用“大量存在”这个词来形容“近亲繁殖”现象的,你只要稍微留心一下,就会发现“近亲繁殖”已经成为我上面说过的我们这个社会普遍存在、人们见怪不怪的社会通行法则。举例来说,有的电影演员或者电影导演的子女往往子承父业,也当了电影演员或者电影导演,至于晚辈电影演员或电影导演是否优秀卓越,完全成为了不得不听天由命的事情,事实上我们看到过不少思想和艺术上都很平庸的“演二代”、“导二代”;有的专家、学者、教授的孩子往往也站到了专家、学者、教授的位置上,在专业选择上甚至也有了精准的对接;老爸老妈是出版社、杂志社编辑,他们的子女往往也能够在出版社、杂志社谋得编辑的饭碗,顶不济也可以搞搞发行、印制之类的工作,总之可以活下来,并且活得比一般人要滋润。有的老爸老妈是著名作家,那么他们的子女如果因为缺乏天分而没有成为作家,也必定会在作家协会体制内讨得某种生存位置,甚至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文化官员,虽然在这些人中有的也混得风生水起,然而从文学的角度说,这些人进行的不过是一种文学“活动”而已,与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造尚有极为遥远的距离,这就是说,他们不过是文坛上另一种形式的“侵入者”,他们的作为仅仅是谋生的手段,与文学的成色好坏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请注意,我们的“文坛”是带有体制色彩的社会组织的一种形式,这些“侵入者”当然是占据了这个社会组织的某个位置的,这意味着他很有可能有意无意排挤了有天分成为作家的人在这个社会组织中的存在,即使是在在最低层面甚至也造成了问题,那就是在就业权利的社会分配中,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
之所以造成这种现象,确实有历史的原因,那就是建国以来曾经将职工退休退职、子女顶替参加工作作为一项劳动就业制度,可谓是行之有年。子女顶替,又称接班顶替,是指父母退休、退职后,由其子女顶替空下来的名额,进入父母原工作单位上班。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种制度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单位成为很重要的招工方式,在解决就业问题上发挥过积极作用,这也是当时几乎人人耳熟能详的社会现象。随着劳动就业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公平、竞争、择优就业观念的深入人心,80年代末期,这一历史性的就业制度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1990年12月8日,劳动部发出《关于继续贯彻执行〈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的通知》,指出搞内招、顶替,不仅违背《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的基本原则,不利于企业选用合格人才,影响职工队伍素质的提高和人员结构的合理化,而且会形成企业内部亲缘关系复杂,给企业管理带来困难;目前国营企业吸收劳动力的能力有限,一些企业又处于停工停产状态,采取内招、顶替的做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难的问题。对违反招工原则搞内招、顶替的,要进行批评教育并予以制止和纠正。自此,子女顶替这种社会现象基本消失。(参见王爱云:《我国历史上子女顶替就业制度的形成及废除》,2009年)
也就是说,我们议论的话题,并不完全是某种政策凭借着社会惯性自然延伸的结果,它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为地扩展了,甚至可以说,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近亲繁殖”成为了一些人利用体制缺陷谋取个人利益的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现象,成为了一个不可忽视、不可回避的社会公平正义与否的问题。
话说到这里,人们自然会产生一个疑问:不是一直都说社会有自净功能吗?没有资格的人站到了有资格的人应该站到的位置上,社会难道不会将其淘汰吗?答案是,“淘汰”是有条件的,在我们所说的社会人群中,有的人遭到了淘汰,譬如平庸的“演二代”、“导二代”丢失了票房,被观众抛弃,被市场抛弃,再也没有人愿意给他投资,他自然也就会消停下来,把位置让给更有才华的人。这是市场规则带来相应的职业性质和职业特点改变所决定的。不幸的是,并不是所有“职业”都具备这种“市场”的性质和特点,事实上,相当多的行业是不具备或者说完全不具备这种淘汰功能的,相反,有些行业往往会表现出一种对“近亲繁殖”现象的体制性呵护的功能,使这些人可以毫无风险地在原有的位置上舒适地存活下来。大专院校、社会科研单位、包括作家协会在内的各种协会、文联组织之类的官办机构,都具有这样的特点。不信你可以查一查,在此类性质的单位里,有多少人是具有“子承父业”、“近亲繁殖”色彩的。
可能有的读者不以为然,说:“陈行之先生,我觉得你过于敏感了,诸如此类甚至更让人堵心的事情我们见得多了,你说的这些事情难道还叫事情吗?”
我承认,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事物中,确实有比我说的这个事情更严重的事情,譬如由于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而导致阶层固化,权力体系内部严酷的权力斗争以及无所不在的利益纷争所导致的对社会和谐与稳定的破坏,更能影响决定社会的存在样态,圈子文化、裙带关系、“近亲繁殖”之类确实不是什么很大的事情,然而我们也必须警觉到圈子文化、裙带关系、“近亲繁殖”现象对社会所起的销蚀作用,这种销蚀作用的严重程度,我认为是远远超乎人们想象的,其指标性的结果在于:它严重堵塞了社会上升的渠道,最有才华的人往往被挡在了专业领域之外,社会创造力受到压抑,由此进一步导致阶层固化……这对于一个寻求崛起的民族来说,绝对不是什么好事情。
那么“近亲”究竟是什么“繁殖”起来的呢?它需要哪些必要条件呢?
3
在探讨这些问题之前,我先说说“人才”这件事吧,我认为它们之间是有关联的,甚至可以说人才问题更能从实质上体现社会上升通道通畅还是堵塞的问题。
古往今来,人才问题都是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人们在怎样为人才脱颖而出上可谓是殚精竭虑,想尽了办法。在中国历史上,人们说某位皇帝做出了什么什么贡献,具有什么什么样的伟大品格,往往都要说到他对人才的尊重,说到他胸襟宽广、广开言路、使贤任能、克己纳谏的道德品性。大家熟悉的唐太宗李世民就是中国历史上知人善任、虚心纳谏的一个很好例证。人们津津乐道的把中国农业社会推向鼎盛的所谓“贞观之治”的出现,固然有政治、经济、文化诸般成就作为支撑的原因,然而你也必须注意到,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由于李世民的推动,社会上升渠道贯通,即使贫寒人家的子弟,通过不断完善的科举制,也能够得到发挥才华的机会,找到相应的位置,全社会呈现出一种奋发有为的气象,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如果唐太宗不是这样的人,而是像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的胸襟狭小、嫉贤妒能、专权跋扈的皇帝一样,由着性儿任人唯亲,由着性儿胡作非为,甚至由着性儿摧残人才,那就不可能有什么“贞观之治”,事实上,很多没有成色的皇帝就是这样糊里糊涂丢掉江山的,猜忌成性、滥杀文武大臣的崇祯皇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崇祯皇帝哭哭啼啼吊死在煤山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意识到没有,他今天的结局实际上早在凌迟处死袁崇焕之时就已经被确定了。
说人才为什么扯到了皇帝呢?这是因为,人才问题与权力问题或者说与权力的行使问题息息相关,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才能够捕捉到从历史深处绵延而来的某种脉络和机理,“近亲繁殖”这件事儿就隐含在这种脉络或者机理之中。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一句俗话,叫“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我觉得这句话挺好的。好在哪里呢?好在它用浅显的语言道出了权力的本性,那就是:权力具有裁决人或者事物的是与非的强制力,它所认定的东西,你是没有办法否定更没有办法推翻的,这就造成了一种后果,即:在一定范围内——我通常将其称之为“权力场”——权力就是上帝,而上帝是不可违拗的。
权力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几乎涵括所有具有强制与服从机制的领域,譬如老板对管理层和员工形成权力,县委书记对其治下的所有官员和百姓形成权力,警察对司机形成权力,老师对学生形成权力,城管对小贩形成权力,幼儿园阿姨对孩子形成权力,牧羊人对羊形成权力,等等。一般来说,强制与服从会自然形成为一种场域,我所说的“权力场”指的就是这种“场域”。人都是活在“权力场”中的。
人活在权力场中这件事,正常还是不正常呢?我认为是正常的,这是社会的基本结构,你是没有办法改变也不可能改变的,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秩序”——你想,如果有一天司机突然把车停在警察面前,命令警察把警察证拿出来,并且公然给警察记了12分,然后扬长而去,这还成体统吗?那要是羊把牧羊人围堵起来,喝问道:“你丫凭什么管我们?!”这世界不是得乱套?
既然这样,那为什么还有“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之类的事情发生呢?具体到我们的话题,实际上“行”却被认为“不行”的人,怎么就会得不到尊重呢?怎么就会被排挤到角落里去了呢?这就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即权力性质的问题了——这个问题与人才问题息息相关。
4
现在我们假设有一个叫赵甲的老板,也不知道怎么了,成天跟公司里最有才华最有创造性的科学家钱乙过不去,有一天竟然把钱乙堵在楼道,说:“你以为你是谁?我实话告诉你,公司是我的,我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就是这!你看着办吧!”钱乙眨巴眨巴眼睛,一定以为自己撞见了鬼,读者也会指责这个老板说:“公司既然是你的,公司的发展一定是第一位的,你说出这样的话,这不是在用左手砍右手吗?你要是这样做,没有别的解释,只能说你丫神经不正常,疯了。”
读者的指责恰如其分,因此我们的这个假设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读者的指责道出了这里边的真谛:权力是老板的,公司也是老板的,他们是一体,老板不可能无视公司的利益而轻率地使用权力,这既是社会机制的约制,也是人性的约制。然而我必须强调,诸如此类的情形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却是有可能发生的,那就是在“单位所有权公有”的领域。
在“单位所有权公有”的领域,权力是个人掌管的,而公司是国家的或者集体的,这就有充分的条件让公司的管理者以个人好恶替代对公司前景的考虑,做出“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的荒唐事情来。这样的事情,在国家行政机关尤其司空见惯,它所导致的往往是任人唯亲、钻营投机、人身依附,最有才华的人得不到任用,放不到合适的位置,人才的上升通道被堵塞。由于是国家行政机关,它的消极后果不像公司那样可以用数字图表的形式显著地显示出来,顶多表现为效率低下、国家行政能力锐减,而这似乎又是很难捕捉到个人的显性责任的,也正因为如此,此种现象才绵延不绝,很难得到遏制。有在国家行政单位工作经历的人,几乎都经见过有才华的人由于不会来事而无法获得升迁、无能之辈却由于依傍了某位领导而上升到台面招摇甚至胡作非为的事情。为什么在世界范围内几乎所有国有企业都是低效的?这就是原因。
此种情形,让我想到“管道效应”四个字:如果人才上升通道被堵塞了,那么就会形成一种回流,这种回流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逆向淘汰”。在我看来,“逆向淘汰”是一件极为严重的事情,它像病毒一样在社会肌体内部不断地吞噬健康细胞,这种吞噬虽然不太可能瞬间造成社会死亡,但它对社会肌体健康造成影响却是毋庸置疑的。最近一些年我们常常听到“塌方式腐败”这个词,说的是某地不是一两个官员腐败,而是所有官员成窝的腐败,我想,如果在此之前没有“逆向淘汰”机制的长时间培育,让具有相同恶劣品性的人走到一起,“蛇鼠一窝”,诸如此类的事情是很不容易发生的。
我曾经亲眼目睹在“所有权公有”的单位里,权力者为所欲为拨云弄雨、颠倒是非、指鹿为马,“说你行行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毁掉一个单位的事情。这绝不是个别人的责任或者说罪恶,我们甚至也不能由此对某些人进行道德谴责,这是一种比个人作用强大得多的体制性缺陷,人性中的丑陋只不过是利用了这种缺陷而已。遗憾的是,截至目前这种缺陷也很少被人所注目,它往往被“嗨,世事就那么个样子”的无奈感叹所遮盖,只有那些在事情当中的人,才能够感受到切肤之痛——我相信读者中就会有这样的人。
5
导致社会上升渠道阻塞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上面提到的裙带关系,即所谓的“圈子文化”。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很容易结成一个又一个“圈子”,不在“圈子”里似乎寸步难行,从而造成一种极为特殊的社会生态,读者对此一定不感到陌生。
上世纪80年代我在西安工作的时候,还是一个初入文坛的青年。与80年代的社会氛围有关,那时候文学青年都怀着很大的冲力,想写出优秀作品。而“优秀作品”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能不能在全国著名文学刊物上发表。有一段时间,西安突然冒出了一个连续在全国著名文学期刊发表作品的女作家,我拜读过这位女作家的作品,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因此在情感上也就没有什么“敬佩”、“羡慕”之类的东西。交往比较深入了,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发现这位女作家的作品竟然是摹写出来的——她亲口告诉我,写小说的时候,她会先找一个范本放在稿纸旁边。这让我十分惊讶,它几乎颠覆了我对“文学创作”概念的全部理解。我不知道她这些可以用“平庸”两个字形容的作品是如何在遥远的上海、北京等著名文学期刊上发表出来的。
在这位女作家身上找不到答案的东西,我却从另一伙人身上找到了答案。
那时候文学期刊很少,每个省只有一个文学期刊,陕西省也是一样。我刚从延安调到西安,虽然也有资格参加文学界的活动了,但并不在作者队伍的核心圈里,那时候这份期刊的核心作者队伍,是几个带有农民文学色彩的业余作者,在我印象里,他们就像占领者一样占领了那份期刊,连篇累牍发表的都是他们的作品,远离西安的那些业余作者,很难获得发表作品的机会。这一点,我如果还是在延安,是绝对不会知道的。纯粹用文学的标准来衡量,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也认为他们的那些作品还没有脱离农民讲故事的色彩,完全不具备“文学作品”的品格,哪怕是在形式上。然而它就那样存在着,甚至还获得本省评论家很高的评价。
据一个了解内情的人告诉我,这伙人跟作协和杂志社领导以及编辑都混得很熟,形成了所谓的“圈子”,你来我往,饭局不断,所以他们的作品才能够长期占有期刊版面。那个刊物自创刊以来破天荒发表中篇小说,发表的是我的《小路》,我很感激刊物编辑对身处圈子之外的我的支持。随后我就听到,那伙儿风光无限的作者对刊物发表我的中篇小说几乎是义愤填膺、暴跳如雷的,有人甚至闹到了编辑部,指责刊物违背了创刊宗旨和长期以来的风格,不应当发表这种带有欧美文学色彩的具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小说,跟他们很不相熟的我,竟然引起了他们很大的敌视。那时候我刚30出头,还说不上有什么丰富的社会经验,因此很为这种现象所不解。我清晰地记得,我私底下对这伙人的评价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能够成为真正的作家,我的这个推论后来很不幸得到了证实。现在,就像过眼烟云一样,那些曾经的风云人物早就被时间淹没了,那些当年显赫喧嚣的作品也都泥牛入海、销声匿迹了。
路遥曾经当我面调侃这伙人说:“文学是一种活动,这些家伙都很聪明。”而我在想——也许是我刚从延安来省城不久,深知业余作者不易的缘故吧——那些在偏远地区做着文学梦的青年人呢?那些接连接到退稿信的作者中,万一有很有天分的文学人才呢?不就错失了发表作品、登上文坛的机会了吗?不就被这伙人排挤了吗?现在想起来,我也真是天真,社会就是这样,社会的机理就是这样,在漫漫的人世间,人因利益而结盟,人也因利益而散伙,人生的悲喜剧每时每刻都在上演,这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如果不是要议论社会上升通道的问题,即使是我也很难回忆起年轻时代遇到的那些事情。
让人慨然的是,那些事情如今在全社会范围内不但仍旧广泛存在着,仍旧在更大范围内发生着,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也就是说,无数没有裙带关系或者不善于搞裙带关系的人,无数无心在形形色色的“圈子”里拨云弄雨的人,是无法站到他们想站到的位置上去的。譬如,杂志社、出版社都有自己的所谓“核心作者队伍”,按说这些所谓的“核心作者”在那个领域应当是拔尖的人才,发表出来的都是拔尖作品,可是我们实际看一看,有多少不忍卒读的平庸之作在泛滥?!我不愿意指责说这些杂志社、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中掺杂了不便言说的肮脏的东西,但是我们无法否认,个人好恶、利益得失在其中一定起了很大的作用。我曾经听到有人愤而谴责某些杂志社、出版社“成为了利益交换的场所”,我认为他们的谴责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而所有这些上不到台面的“作用”之所以发挥作用的原因,或者说所有这些作用的核心支撑,仍旧是我前面已经说过的“单位所有权公有”的原因。在“单位所有权公有”的状态下,任何人都可以不为各自的杂志社、出版社的名誉、效益、命运负责,任何人都可以用自己所拥有的权力去交换他个人想要的东西,这时候你还说什么人类精神产品的神圣性?!假设这个单位的所有权不是公有的,除非一个人特想把自己掐死,哪一个杂志社、出版社经受得起工作人员如此不死不活的懈怠和几乎半公开的利益交换弊端?!那时候,我们还看得到大量平庸之作泛滥成灾吗?我们还看得到不具备基本文字能力的人成为全国著名作家吗?那还看得到评论家故作高深地评论那些垃圾作品吗?!一切的一切都会不一样了啊!
不得不承认,尽管经历了改革开放,然而在为所有人创造公平发展的机会上,我们似乎并没有前进多少,在某些领域我们甚至是后退了。
6
我们在谈论人权的时候,往往用“发展权”概括西方学者所谓的人权,认为人的发展权利高于其他经常被人强调的各种权利。既然如此,倘若在社会的实际运行中,一部分人的发展限制了另外一部分人的发展,或者说,一部分人的发展总以另一部分人被剥夺为代价,那很显然就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了,这一点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警觉。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对诸如此类问题的深刻洞见,仍然包含在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论述之中,身在其中的我们反而有些蒙然坐雾,不知就里。即使占据高位的煌煌思想大家,也似乎有些麻木,并没有有针对性的研究成果出来,更不要说系统性的理性思索和理论建树了。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往往不具备直面现实的勇气,我们更没有说出真相的胆略,甚至连说出思想的能力都要退化了,而这种状况不是一时半会儿就可以改变的。这其实同样也是发展的问题——没有一定条件的社会发展,人是不可能得到全面发展的;反之,如果没有人的前面发展,社会发展也终将会成为不可能。人,无论尊卑长幼,都逃不脱这种规律的制约。
我们换一种方式表述:只要我们不封闭自己,只要我们的眼界是开阔的,只要我们有胆量不忌讳什么,我们就会发现,关切人的存在,关切人的发展,早就成了镌刻在人类精神殿堂上的重要内容,很多厚重思想的阐述,早就梳理清楚了我们正在思考着的这些问题的脉络,那些连篇累牍的格言警句式的提醒,总是在告诉人们,一个社会如果失去了正义的品格,那么它一定会麻烦不断,它的结局也一定会是悲剧性的。
我记得密尔在《论自由》一书中曾经特别强调:“个人的自由必须约制在这样一个界限上,就是必须不使自己成为他人的妨碍。”而我们正在议论的裙带关系、圈子文化、“近亲繁殖”等等丑恶的社会现象,无一不是以一部分人的自由(发展)妨碍另一部分人的自由(发展)为代价的,用密尔的话说,这就等于一部分人的自由超越了界限,变成了对另一部分人的自由的妨碍和侵犯。值得警惕的是,如前所述,这种侵犯不仅持续性地发生着,而且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有了更宽广的范围,它的严重程度也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