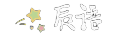暂无AI摘要
暂无AI摘要 一年3600,刚落地没几天的育儿补贴政策热度甚至还不如武汉大学以及它的“优秀”毕业生杨小姐。
我家孩子现在刚满9个月,每年3600元的补贴金额,和在青岛这样的城市实际养育一个孩子所需的高额支出相比,是极少的。
更何况政策一出,奶粉尿不湿集体涨价,一如家电国补一样。
但是,是什么导致出台了这样的补贴政策呢?
还记得庄子在《逍遥游》中描绘的鲲鹏吗?
庄子写的是:“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但是鲲鹏也需要凭借风的力量才能起飞,“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
风是什么,鲲鹏又是谁呢?
制度过去构建出了很多东西,这些东西被设计出来,目的是为了托起他们想象中那样发展的人和社会,以著名的“bi-wealthy”论为典型代表。
但是现在,现实印证了马克思的观点: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状态是在加深的。生育率下降不可逆转的原因,正是这种相对贫困加深的状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不可逆转。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了不去做,或者干脆就是买不起那个被制度设定好的样子。那么,制度过去提供的那些东西,又还能托举起谁呢?
过去那套曾经能自我维持的体系,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默不参与的情况下,暴露出了自身的问题与应对的困难。
老子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
长久以来,制度实际上是在按照这样的逻辑运转的:它预设了每个人必定会按照既定的路径去买车,于是车市就把价格定得很高;它坚信血脉传承和家族延续的重要性是无法动摇的,那么天价彩礼就在“爱情”与“责任”的名义下,变得理所当然而且难以撼动;它认定了繁衍后代是每个人不可推卸的人生使命,于是家庭传承就变成了对人的要求、督促和施加压力的核心依据。
制度在推动人去追寻这些目标时,无形中强化了这些路径的“刚性”和“必需性”,仿佛它们必然会被无限“张之”、“强之”、“兴之”。
然而,现实情况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
现在的车市,热度已经不如从前了,即便是那些非常昂贵的汽车品牌,也不得不放下原来的姿态,开始大力提供折扣优惠,厂家表现得非常着急了;在很多地方,彩礼已经不再是年轻人结婚时背负的沉重负担了,甚至一些地方的政府主动废除了高额彩礼的习俗。
当出生率大幅下降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时,那份经过很多呼吁和等待才出现的补贴政策,它的补贴额度之少,恰好反映出了制度在这种焦虑之下的两难困境。
一方面,补贴少了没什么用;另一方面,补贴多了又担心“高福利陷阱”、担心三年后弃养、增加杠杆率等问题。
年轻人集体选择了一种疏离的态度。
这并非消极怠惰,而是在压力下的一种策略性退出。这种选择,在精神气质上,与庄子所说的摆脱外在依赖(“无待”)的境界有某种跨越时空的呼应。
他们都试图拒绝被某种强大的、预设的规则完全定义和束缚。庄子追求的是“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超然逍遥,是一种在清醒认识的状态下,摆脱了功名之累的心灵自由。
当结婚、生育、买车买房这些事情,被不断地渲染描绘成人生必需的基础时,一部分年轻人却选择悄悄地离开了这场预设好的生活游戏。
“爷不要了。”
这并非在困难面前消极地认输,而是不再愿意把自己的精力和资源,消耗在与那些不合理规则的周旋纠缠上。也就是说,当拒绝合作被选择成为一种策略手段时,掌握规则的权力体系就只能放低姿态,尝试用给予的方式去寻求缓和了。
“大道甚夷,而人好径。”
年轻人集体选择“不为”,不再对规则所构建的复杂路径俯首顺从,而是以清醒的认知去识破“人好径”这个陷阱,开始挣脱制度提前设定好的路径。
这份沉默无声的拒绝行为,实际上比那些口号喧哗的反抗,包含了更深的意味和力量,它像是一种看不见的力量,迫使运转了多年的既定机制偏离轨道,甚至停顿下来。
年轻人选择退出的力量,虽然起初并不引人注意,但最终使得原先设定只有“鲲鹏”才能“乘风而起”的规则发生了变化。
3600元育儿补贴这个东西,它的象征意义和具体数额一样微薄,反映出了制度试图进行自我调整的努力是笨拙的。
在权力体系无法单纯依靠施压和规训继续有效运转的情况下,改变才被迫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
老子说,世间万物的运动规律是“反者道之动”:制度如今表现出的这种被动姿态,恰恰是整个体系受到反向力量冲击后,被迫转向寻求某种新活力的表现。
年轻人其实不需要高声呐喊,也不需要公开地对抗。
庄子推崇心灵能够在虚无缥缈的“藐姑射之山”自由遨游的境界,其本质就是不依赖于任何外部价值评判也能获得内心的真正解脱。
年轻人集体采取的清醒疏离行动,如同柔弱的流水持续拍打坚固的堤岸。当这种选择“不为”的趋势汇聚了足够大的力量时,自然能让阻挡它的障碍开始松动。
真正的社会变革,其源头常常在于那些被规则所限制的人们,所采取的那种无声却坚决拒绝配合的退出姿态。
当我们决定不再按照他人写好的剧本来扮演自己的角色时,世界的运行规则也就开始被迫地修改它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