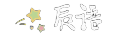暂无AI摘要
暂无AI摘要 长大后我才发现,河北的教育,一直以“服从性训练”为主,没有人觉得它需要被打破。就算是儿时信誓旦旦要打破它的人,最后也或是“终成恶龙”,或选择逃亡,再也不回来 。
这片华北平原的人们,不懂抗争的原因从来不是贫穷或愚昧,而是无力与习惯。
无力去抗争,且习惯了这种冗长而绝望的无力。
1
降生于这片华北平原的我,走过河北学生最普通的路。
从小学开始补课刷题,高中开始进入“衡中模式”,在普通学校做普通人,高三借读“地狱衡水”,最后考入河北省一所还不错的大学。
如果正常的话,我会在这所学校读到毕业,然后回家当一个老师或者公务员,嫁给我的高中同学,生一个或两个继续“为衡水模式”奋斗的孩子,平淡而幸福的度过一生。
可惜从小到大,我实在读过太多书了。
因为读了太多书,我从小就知道双水村外有个大世界,从小就知道我与外边的同龄人是不同的。
儿时记忆里的小城总是阴着天,后来才知道那是雾霾,是为了“保卫首都蓝天”而迁移的重工业制造的,虽然最后河北与北京的蓝天都没守住,但好在我们呼吸的也是同一片空气。
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就变成了早六点起床上课,晚六点放学回家的“高考预备役”成员,周末则奔波在大大小小的文化课补习班里。
那时的我喜欢看杨红樱之类的儿童读物,小时候的我很不解:为什么书里的校园生活永远多姿多彩,有各种各样的兴趣小组、文艺活动,而我的世界里却只有语文数学英语。
到了五六年级,被老师“按头补课”的我连寒暑假都不复存在了,自己从小上到大的民舞课因为没有合适我年龄的老师和同学而被迫停掉——那时,我已经和比我小三四岁甚至六七岁的小朋友上了至少两年的课了。
在河北的小城里,是没有十几岁的、要小考的女孩还在学跳舞的——除非你天赋异禀,父母也愿意每周奔波二百公里把你送去市区学。
很不幸,成年了之后才勉勉强强一米六的我并不算“天赋异禀”的那一个。于是母亲在某天课程结束的下午旁敲侧击地问我“要升初中了,舞蹈课要不别上了”的时候,我坐在副驾点了点头。
有没有梦想和热爱碎掉的声音,我已经记不起来了。
小升初那年,我“正规升学”进入了全县唯一一所不用考试的中学,找关系进入了重点班。虽然依然是早六晚六的作息,但好在学校管的不严,教学质量也很高。
初中三年,我没再跳舞,因为碰见了一个好班主任,看到了我的“天赋”后带着我全省各地参加写作比赛,让我重新有了新的热爱和人生目标。
为了“报答”班主任,我的初中开始发奋图强,开始明白自己要努力学习走出小城,我开始认为“所有人都在努力”,“要努力才有更好的未来”。
青春期的我开始明白,我要足够努力,才能过上我想要的人生。
初三那年,因为不想离开家,我和县中的重点班签了保送协议,这次是我凭借我自己的真才实学考上的。
没有反叛的初中生活让我的一切都变得格外顺利,我渐渐发现,似乎顺从体制、顺从规则、顺从苦难是我完成梦想、走向人生正规的不二选择。
2
高中时,我的书桌上写了这样一句话:
“当你背单词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算数学的时候,南太平洋的海鸥正掠过海岸;当你晚自习的时候,地球的极圈正五彩斑斓;但少年,梦要你亲自实现,世界你要亲自去看;当你为未来付出踏踏实实努力的时候,那些你觉得看不到的人和遇不到的风景都终将在你生命里出现。”
这段话是励志,更是自嘲。
虽然是县中,但我经历的依旧是河北学生十几代如一辙的衡水模式和绝对服从。
无特殊情况不能走读,每天五点钟起床叠豆腐块,一个月不能洗澡洗头,没有音体美和课外活动,每一个假期都是无尽的补课所撑起的,班主任和年级主任掌握着绝对话语权和“执法权”……
我们所有的时间和思想,从进入这所学校,成为一个河北高中生开始,就是为了高考而服务的。
因为是重点班,所以身边的大部分人都默许了这样的管理,除了我在学校“高压红线”下偷偷谈着的男朋友。我和他不理解为什么可以一个月不洗澡不用手机、不理解为什么要五点起来叠豆腐块然后人贴人跑操、为什么每天十五分钟的吃饭时间让我们连饭都吃不上。
我们两个偷偷翻墙回家、逃掉跑操,双双被挂在学校的“处分栏”上。教导主任苦口婆心的劝我们:这些享乐的东西可以到高考后再慢慢体验,现在要以学习为主。
现在听来甚至有一丝想笑,原来洗澡、吃饭这样的正常生活需求,在高考面前被叫做“享乐主义”。
年级里一个师大刚毕业、比我们大不了几岁的小老师偷偷告诉我们,高中不能太好太快乐,要不然你们就不想读大学了。比起年级主任的“不要享乐主义”,小老师的语言让我更能接受。
更有趣的是,根据校规,谈恋爱的两人里一定要有一个人退学。不过我们两个连手都没牵过,我们一口咬定“只是好朋友”,学校抓不住我们的把柄,加上我家和他家关系还不错,最后只是把我们两个分在了两个不同的理科班。
高中三年,前90名的重点班要不停流动重新分班,每班30人,我和他却因为一些“特殊照顾”,从来没有分到过一个班。
因为我们两个,学校的“超常交往”变成了男女不能同桌吃饭、并排走路,否则就按照谈恋爱处理。
后来读了大学才理解,这样的行为只是为了“消除个性”,我们不是一个独立的、完整的人。作为高考大省的一部分、在高考工厂的重压下,我们只能成为一个高考机器,一个没有自我、没有个性的机器。
身为学校里为数不多的走读生,晚上十一点钟回到家,我可以打开手机看一看外边的世界。
手机里,一百公里外在市区读书的朋友飞向全国各地参加模联比赛,二百公里外的北京姑娘逃学去西藏、借家长身份证搞公众号做到十万加。
而我,心有一片海,面前却只有做不完的五三和习题、上不完的早六和自习,诚如老师所言,我想做的事、想看到的东西都在我倍加努力才能到达的未来。
高考结束后,我稳定发挥,以570分的优异成绩考入了省内的一所二本院校。
毕业宴会那天,大家——包括我市区或衡水读书的朋友才互相发现,大家基本重聚在了石家庄大大小小的学校里。除了初中的年级第一考去了北京一所211,走出河北的寥寥无几。
我和我最好的闺蜜,学校甚至“住对门”,我的交际圈没有丝毫改变。
父母亲人对我希望百倍,觉得终于熬出了头,但是,我退学了。
在这所大学里我意识到,我并没有得到我赤诚着追求的自由。
大学,对我们或我而言,不过是一场巨大的骗局。
读过的十八年书告诉我,它是时候被打破了。
我的第一个大学生活,甚至不如我北京朋友的高中。校内等级森严,有完整的早晚自习和查寝制度,没有疫情的日子里,大一出校还要有辅导员的审批。学生会的学姐那么高高在上,她们说:“你们做什么我都知道”,“辅导员会听我们的,你们要乖一点”。
我并未得到我向往的大草坪、光芒万丈、小酒馆与彻夜不归,我拥有的只是比衡水模式好了一点的、所谓大学生活。
身边的人万分感恩,毕竟他们终于考入了一所大学。
而我,只觉得我被欺骗了。
现在,我退学复读后,经历了一年努力到感动自己的衡水黑暗岁月后,在南京的一所大学读新闻。
之前有疫情的时候,我可以和我的朋友一起在周末的晚上通宵逛鬼市、大家通宵拍作业、在不断电的寝室里赶DDL。
那时我才发现,走出来对一个河北学生来讲那么复杂,那么痛苦。
那些留在河北的朋友与我渐行渐远,他们毕业后回到老家,做公务员做老师,让孩子们继续这样平凡普通、无法批判却又都是错的日子。
而我,逃离了,不会再回来了。
3
时至今日,我也并不知道河北的教育模式到底有没有可批判性。
我在父母的支持下获得了自由,且不被父母理解的“彻底离开了家”。但我总能想起县中的小教室,暴雪压塌了对面的车棚却没有一个人敢抬头的冬天。
那个教室里,除了有读着小说、袖子里藏着mp3偷偷听着南山南,在监控下谈恋爱的我和同桌,还有面前家庭年收入只有5000、到了高中才开始学英语的小个子姑娘、因为考不上二本家里也承担不起三本学费而退学去北京卖房的女舍友、父母连字都不认识的男班长。
我一直记得那个冬天的家长会,我穿着母亲精心挑选的裙子,化着淡妆接待家长,母亲和面容姣好的班主任身上各一件貂皮大衣,在一旁寒暄着衣服的质感与价格。
时至今日,我都觉得它残忍且昂贵。
那个寒冷的早晨,在靓丽的母亲的对比下,他们的父母那么疲惫、皲裂的手签好了名字、老得像是我的奶奶。
他们对我恭敬且羞涩,似乎还有一种自卑和无奈。
后来的好几年,我都在吐槽母亲那天的盛装出席有多么的不合时宜,母亲则总是一边看着手机里辛巴的直播一边笑着解释:“我真的不知道你的同学家庭情况都是这样的”。
是的,和衡水借读时一个家长为了给自己孩子改善伙食、买了全班的麦当劳相比,我所在的县中才更是河北孩子的真实写照。
那一瞬间,我不仅没有优越感,反而有一种不可言说的羞愧感和无力感。
对我而言,衡水模式只是我选择要走的、且随时可以不走的一个plan A。
可对他们来说,这是唯一的、最后的出路和选择。
他们,除了衡水模式、噩梦大学,别无选择。
能够考上一个大学、能够不进厂打螺丝、在太阳下干工地,对他们而言已是改变命运了。
正如我开篇所言,这片华北平原的人们,不懂抗争的原因从来不是贫穷或愚昧,而是无力与习惯。
无力去抗争,且习惯了这种冗长而绝望的无力。
到目前为止,我也不知道除了衡水模式,还有什么能改变河北孩子的命运。
是郝局长被推翻的素质教育、学生讲课、三疑三探吗。政府大楼下反抗素质教育的人潮那么汹涌,他们簇拥着应试教育,簇拥着孩子逆天改命的希望。
是一代又一代学生的自由反抗吗,衡水模式下学校的压热搜、“给处分”的善意“恐吓”,在某种程度下,似乎也保全了我们与他们的未来。
时至今日,见过外明世界的我,能选择的不过是回到老家,成为一个普通的老师,看着孩子们走我不想走的路,变成那只自己反感的恶龙。
或者,往前走,拼命往前走,再也不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