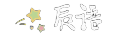暂无AI摘要
暂无AI摘要 平权:未竟的事业
关于最近的女权主义与男权主义风波,我本是不想发声的。毕竟论战前进的交锋太过残酷而荒诞了,而我于某一个清醒的旁观者入场之后,总归显得像是在打圆场。黑格尔曾经说过:扬弃一个已经僵化的二元对立,是理性唯一的旨趣。但在今天看来,这样的乐趣反而显得有些轻浮与置身身外。
但去探讨这样的「扬弃」总归还是必要的。否则我们就会陷在这场没有意义的斗争之中——毕竟这双方的每一方的愤怒都不是为了争斗本身。不论是男权还是女权,其是都在寻找自己的「正义」——他们想要「得到本应属于自己」的东西。正是这种对于主标标尺的偏离,让我们感觉到剥夺与侵犯,以至于我们觉得应当向入侵者索回本属于自己的东西。
然而斗争的双方——更为具体的说是其中的大多数人——忽略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他们心中的标识本是同一个,只是在历史的变动与种种不幸之下才分道扬镳。这个共同的标准就是「性别平等」——不论一个人是男性、还是女性抑或是其他的性别,都不应因为自己的性别而遭到歧视,或者失去应属于之的社会资源。同等学历与技能的女性应当获得与男性一样的工资与尊重、同样限于失业的男性与女性应当获得同等的领救济的机会。
但这个目标依然始终没有被实现,现代性仍是未竟的使命。当前的中国,女性的平均收入只有男性平均收入的60%。
同工同酬、尊严平等:这是现代性曾经许给我们的承诺,亦是我们建国以来一项的追求。那个年代为了针对过去男尊女卑的现实,我们提出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这曾经极大的改变了男尊女卑的状况,那个年代的电影与文学作品之中,女性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主权。当时的社会主义社会男女的工资差距几乎缩小到了可以忽略不计。但在那个时代,女性依然受到着两项隐性的经济社会压迫。首先,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强调家庭的作用,以至于女性在获得工作之余被迫背上了承担家务的责任。其次,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僚精英内部依然存在着隐性的性别歧视。以至于依据统计结果来看,大多数的高级职位仍被男性精英占据。

而在改革开放之后,男女收入差距的拉大就可谓是一骑绝尘了。女性平均收入从男性收入的80%下降到了60%。这背后反映出来的是国有单位制向市场企业制转移过程之中,中下层女性劳动者的地位极速下降,以及一系列传统男尊女卑概念的故态复萌。
因此,总体而言,在当今中国的女性依然是受压迫受歧视的。甚至当前女性的平均教育水平高于男性这个事实也没能扭转女性在职业市场上的劣势地位。这一方面来自于女性承担着社会再生产的沉重义务——即生儿育女——一方面也是因为当前的家庭内劳动仍大多数交给了女性,而最后也最为重要的原因,则在于显性或者隐性的职业性别歧视。如果说我们可以较为容易的消除显性的职业歧视——比如直接的大众观念与面试过程之中的差别对待——当前固化的性别分工意味着女性只能拿到中低端的职位。
在今天去探讨「男权」本身毫无疑问是可耻的。若你已经放弃了「人生而平等」这样的基本原则,那我对此无话可说——我已经不屑于与你说话;但如果你作为一个实质上享受着性别霸权的男性,依然想把自己的夺权行为粉饰为平权,那可以说是厚颜无耻、道貌岸然了。

二.「女权」:一种「新种姓制」?
但与此同时,我并不认为当前许多所谓的「男权主义者」真的支持性别歧视。正如上个世纪乃至更久远以来兴起的女权主义、是源自于女性对于自己人格被剥夺这一事实的愤慨;当前的一些所谓的「反女权主义者」也有着合情合理的愤慨。这个愤慨就是当前国内的一部分女权确实没有如同一个平权者一样行事,而是把女性自贬为一个新的贱民种姓、随后想要把当前的婆罗门打成贱民、让自己爬上高种姓的宝座。
我们不妨参照一下当前的「Me too」运动,或者历史上曾经女权主义者的观点。真正的女性主义不是想追求女性的权威、更不是想歧视男性,而是想追求成为平等的人。他们从不发真诚的呼吁着:女权主义者也是在解放男性——当社会把贬为女性变为柔弱的淑女时,同时也在把男性逼成残酷的暴君。这种女性主义是人类进步伟大的舵手、是人类的光。她们的所作所为如同马克思所说:作为一个被压迫阶级,只有在解放一切阶级之时,才能迎来自己的解放。
但当前的女权主义似乎已经退化成了一种新的种姓主义。他们并不想消除当前男女对立与性别分工的事实、而是享受着这样种群之间的不平等,只是想让自己成为新的压迫者。他们不是想让人类从性别的范畴之中挣脱出来,而是想让「男性」取代「女性」成为卑贱的代名词。而这可恶的一点在于:许多大城市中的精英女性甚至根本就不在乎与自己同样性别的悲苦姐妹,她们宁愿花整天的时间去骂一两个贫困的男性,也不愿意花些时间与钱帮助一下那些农村真正受压迫的妇女。
这一点上,章北海说的是有道理的。口号与认同上,人们会组成各色的小圈子;但在行动上,人们的行为总是沿着「阶级断裂线」分开。

向「平等主义」致敬
在文章的结尾,我倒也不想去重提「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了——富人对于资本的占有、对于穷人的剥削;与男性对于家庭的占有、对于女性的剥削是相同的,就是很显白的事实。我反而想谈的是一些更为实际的事情——那些想要追求公正的女性与男性该做些什么?
毫无疑问,消灭「有产阶级」并不能够确保女性的解放、就好比说消灭「有产阶级」不能够直接带来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一样。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都不单纯有两个阶级构成,其中总归有种姓制度的成分。这意味着不同的族群之间还有各种精妙与细微的等级差距、文化上贵贱之分。因此,简单地将女性主义的斗争推后、收纳在阶级斗争之下是不明智的。可以说「女性的解放」是「阶级解放」的同路人。没有女性的解放与平权,社会革命总归是空泛的;而没有无产阶级最终的胜利,女性的解放无非就是让有产妇女可以压迫无产妇女罢了。
因此,当前的当务之急并不是争论男权主义还是女权主义,哪一个是真正受损的一方;而是去找到那个已经落满了灰尘的「正义天平」。而这个天平上的铭文之中,既不会写着「男人」,也不会写「女人」,只会写着一个简单的答案:人是万物的灵长,人生而平等。
而随后我们就会发现「愤慨」来自于何处——并不是来自女性、也不是来自男性,二是来自于「不平等」本身。女性没有夺走男性的工作,男性也没有夺走女性的工作。我们生活中受到的歧视多半也不是来自于女性和男性,而是领导与上司。全体女性把全体男性变为性奴——如同阿里斯洛芬《公民大会妇女》中的戏谑想象—— 并不会改变餐厅中女服务员或者是女性纺织工的命运;反过来就算一些南拳主义者所意淫的传统社会回归了,他们多半也要回去做长工、或是连工作都找不到、冻毙在男性豪强的官邸门前。而「公正」何在呢?
归根结底,我们会发现那个古老的真理:「压迫他人」的人是无法得到解放的;而只有解放每一个人,我们才能走向自由与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