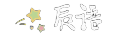暂无AI摘要
暂无AI摘要 载于《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四期
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系 樊秀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并演变为社会帝国主义,除了有它的国际原因外,这主要是苏联国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苏联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了党政大权,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结果。总结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复辟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剖析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社会阶级关系,对于了解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实质,对于我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苏联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了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依然长期存在,资产阶级得以保存和再产生的土壤也依然存在。在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实现以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并没有因为所有制的改造取得胜利而结束。被推翻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虽然失去了生产资料,但他们人还在,必然要千方百计企图恢复失去的“天堂”。正在改造的小资产阶级也不可避免地保留着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仍然要发生两极分化,产生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由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腐蚀、包围和旧社会习惯势力的影响,特别是在分配和交换方面不可避免地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在工人阶级队伍和共产党员以及党政机关中,还会经常产生蜕化变质分子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在文化教育部门也会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同旧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他剥削阶级分子结合起来,形成相当大的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势力。这个社会势力一直在活动着,当时的苏联党和政府曾对此不断进行斗争。例如,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中,联共(布)中央曾经两次作出决定,分别收回被私人非法侵占(有的被出卖、出租)的集体农庄公用土地二百五十多万公顷和四百七十多万公顷,还查获被贪污盗窃的大批牲畜、粮食和钱财。一九五二年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苏共中央报告中就指出,有些党组织的领导人,追求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腐化堕落,“把他们小集团的利益放在党和国家的利益之上”;社会主义企业中追逐利润,搞资本主义经营和贪污盗窃事件也不断发生,有些工业企业的领导人,“竟然企图把这些企业变为他们的世袭领地”;有些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不但不保护集体农庄公有经济的利益,反而自己盗窃集体农庄财产”。
当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的代理人就会要求政治上的统治,要求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全盘改变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公开地复辟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在苏联长期的阶级斗争中,资产阶级总是千方百计地把复辟的希望变成复辟的行动,特别是同社会上旧资产阶级分子相勾结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不断窃取了一些部门的领导权,日益蜕变成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成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代理人。赫鲁晓夫一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集团,就是苏联社会上资本主义势力的总代表。斯大林曾经解决了很大一批钻进党内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但是,苏联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对于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还缺乏经验。在这种情况下,善于玩弄两面派的赫鲁晓夫之流,便在苏联共产党内隐藏下来。斯大林逝世以后,他们见有机可乘,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抛出恶毒诽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施展种种阴险狡诈的手段,篡夺了苏联的党政大权。苏修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党政大权之后,大大膨胀了苏联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把持了各个领域和部门的领导权,从中形成了一个掌握全部国家机器和支配整个社会财富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即新型的大资产阶级。这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就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阶级基础。随着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大资产阶级专政,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也蜕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以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一伙为首的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操纵了全部国家机器,垄断了一切基本生产资料和社会产品,残酷地压迫和剥削苏联的全体劳动人民。
在资本主义复辟以前,苏联工人阶级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占有生产资料,建立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国营经济。随着苏联的国家政权性质变了,国营企业的性质也就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变成了官僚垄断资本主义所有制。在今天苏联的国营企业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委派的经理独揽企业的权力,“在一长制的基础上实现企业管理”。经理有权“占有、使用和支配”企业所属财产,有权“出租”、“转让”和“出售”企业“闲置”的生产资料;经理有权自行确定企业的“编制”,可以自行“招收和解雇工作人员”;法律规定,举凡“撤销机构”、“裁减人员”,或职工“技能不够”、“健康情况不适宜”、“生病四个月以上”等等,都可以成为经理取消雇佣合同和解雇工人的“理由”;经理还有权“对企业工作人员采取奖励措施和进行处分”,有权决定工人补加工资和奖金的条件与数量,可以降低工人工备资、剥夺工人奖金、组织“同志审判会”、开除工人出厂(包括收缴劳动手册),直至送交司法到机关惩处。而工人则只有“遵守劳动纪律和内部规则”,俯首帖耳地干活的“义务”。所有这动些表明,在对待生产资料的关系上,苏联的工人早已不是主人了,苏联国营企业里的生产关系,也早已不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和特权阶层同广大职工的关系,完全是雇佣和被雇佣、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
苏联国营企业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决定了它的生产目的是追逐最大限度的利润。苏修还在党纲中明文规定,必须“提高生产的赢利”。苏修头目也一再叫嚷,“利润和赢利率水平应当成为客观评价企业经营活动的基础”。他们公然宣扬,使投下去的每个卢布带来更多的收入就是他们“经济发展的主要路线”。为了攫取最大限度利润,他们在“新经济体制”名义下,大搞“谢基诺试验”和“科学劳动组织”,推广榨取工人血汗的“科学”制度。他们横征暴敛,巧取豪夺,极其贪婪地剥削工人,以利润和税金等形式无偿地占有工人创造的大量财富,还通过高工资、高奖金和名目繁多的额外收入,把苏联人民的劳动果实攫为已有。据官方大大缩小了的材料,苏联工业中的剩余价值率平均高达百分之二百以上。
在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被大资产阶级专政所代替,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蜕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的条件下,集体农庄这种合作社制度也已变成资本主义的制度。集体农庄是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它的性质取决于“这种形式所包含的内容,问题首先在于集体农庄由谁主持,集体农庄由谁领导”。(《关于农村工作》。《斯大林全集》第13卷)现在,操纵集体农庄领导的都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挑选的人。按照苏修炮制的《集体农庄示范章程》和《集体农庄内部规章示范条例》,农庄主席有权支配农庄财产和资金,出售农业机器和生产资料,决定庄员的劳动报酬和奖金,出租或转让农庄公用的土地,进行变相雇工剥削,用行政,经济手段处罚庄员直到开除庄员资格。他们骑在农民头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个集体农庄主席“在一年内就颁布了一百多项各种各样的处罚令,使每四个农庄庄员就有一个受到处罚”。据苏修报刊透露,农庄主席对农民“起一根鞭子的作用”,“谁也不拿庄员当一回事”。集体农庄庄员必须遵守形形色色的所谓“纪律”和“规章制度”,稍不听话,就会被加上各种各样的“罪名”,道受调动工作、降低收入、解除职务和开除的惩罚。苏修报刊宣扬,有科学技术知识的“专家”才是农业的“支柱”,“‘真正的农民’将不是土地的主人”。经过这种“改造”,集体农庄的一切经营活动已被进一步置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直接控制之下,集体农庄经济已经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
苏联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通过直接掌握全部国家政权,垄断一切基本生产资料,操纵整个国民经济,按照资本和权力的大小进行分配,“按劳分配”只剩下一个外壳,垄断了生产资料的一小撮新资产阶级分子同时垄断了消费品和其他产品的分配大权。他们拥有很大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利用这些权力取得优厚的收入和一般人员无法得到的种种特殊待遇。据外国报刊报道,苏联军队的一名元帅每月工资二千至三千卢布,包括由政府负担的开支,每年实际收入高达约五万美元。“勃列日涅夫同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所有其他成员一样,都有资格在国家银行开一个'敞开支取的户头”,无论他想要什么,都可以随意从中支取多少花多少”。这一帮子人完全是靠掠夺国库供自己挥霍的。为了满足一小撮最大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骄奢淫逸的需要,政府专门设立了一种叫做“特殊仓库”的特种商店,凡是一般人看不到的各种高档商品和西方进口的高级奢侈品,这里应有尽有。例如在克里姆林宫,在格拉诺夫斯科沃大街,在伏龙芝大街国防部附近,在卡门尼桥旁埃斯特拉登剧院附近等处,都有这种商店。稍差一些的,则有为政府各部负责官员、军事首脑等各级党政军人员开设的特种商店。无论那一类特种商店,苏联老百姓连大门也别想进得去。这一帮人,还占有富丽堂皇、设施豪华的住宅和别墅,有专用小汽车和赛车,以及专供他们游乐、渔猎的场所。
除了“合法”的收入和待遇外,这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利用他们窃取的庞大权力,进行各种各样的掠夺活动。如苏联前文化部长就套购大量物资建造了一所价值十七万美元的别墅。一九七三年,在格鲁吉亚首府第比利斯,官员们私分了用作“集体”花园的土地,并用政府的材料建造花房。苏修《真理报》不得不供认这种“花房”就是豪华的私人别墅,其数目在这个共和国就有九百八十九所之多。
苏修叛徒集团为了培植资产阶级势力,在各级领导人员和一般工农群众之间实行一种差别很大的工资等级制度。他们利用特权和各种职务上的便利,通过高工资、高奖金及名目繁多的收入,占有一部分剩余价值。他们不少人还通过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营私舞弊,侵占工人、农民的劳动果实。根据有关资料,经理、厂长、总工程师等领导人的工资同工人最低工资相比,两者要相差十几倍至几十倍。特权阶层在工资以外还利用职权捞到种种补加报酬和优待。企业领导人所得奖金占工资的比重高于工人,他们的工资本来就很高,奖金比重又大,加上企业经理有权决定奖金的条件和数量,更可以为自己多捞奖金。例如,利佩茨克工业建筑托拉斯经理,在一个月内就巧妙地拿了七次奖金,总共一千三百七十五卢布。戈米尔玻璃工厂一个季度发给管理人员的奖金,就占了他们薪金额的百分之一百四十七点二。有时连领导人生日也成了得奖的“理由”。
根据苏修当局一九七〇年的规定,集体农庄主席和总专家的月固定工资可以高达三百卢布。但据苏联报刊自己透露,实际上许多农庄领导人给自己规定了高得吓人的工资。例如,东哈萨克州的大纳雷区列宁集体农庄主席月平均工资为五百八十二卢布,总农艺师和总畜牧师为四百二十八卢布,总会计师为四百四十八卢布。江布尔州麦尔肯区江布尔集体农庄主席的平均月工资为五百十五卢布,阿塞拜疆共和国阿利耶夫集体农庄主席为四百四十八卢布。而阿尔利耶夫农庄中从事大田畜力——手工劳动的农庄庄员的工资,只为农庄主席的七分之一到五分之一。阿拉木图州伊利斯基区的哈萨克斯坦四十年农庄,主要专家每月平均报酬比普通庄员高六倍。根据规定,集体农庄主席等人还能拿到各种奖金,最高可达每月固定工资的百分之四十到五十。集体农庄主席等也可以任意给自已规定奖金。例如,列宁格勒州加青区纪念伊里奇集体农庄主席以对农庄的二十年“有成效”的领导,被“奖给”两个月的工资。甚至农庄里建成俱乐部也成为奖励这位主席五百八十八卢布的理由。他的儿子是农庄的总工程师,老婆是车库调度员,他们都拿到双倍的休假费和双倍的差旅费,以及各种名目的奖金和外快。
工资和奖金并不是特权阶层收入的唯一来源。许多企业和农庄领导人还千方百计地贪污盗窃,压榨人民。建设巴库地下铁道的负责人盗用了价值三千多卢布的配给物资;石油机械安装管理处的头头,通过贪污盗窃,搞到了一座有五百五十平方米住房和一个有游泳池的别墅。亚美尼亚体育用品厂厂长伪造雇员名单,盗窃了三万四千美元。阿塞拜疆一个塑料厂的官员,在黑市出售商品获得二十一万五千美元的巨额收入。里加纺织品公司的领导人,借口出售多余产品,受贿卖掉十吨稀缺的毛纱。格鲁吉亚阿布哈兹许多烟草种植场的领导人,“盗窃的物质财富达数百万卢布”。这个共和国建设银行的某些头头同建筑部第十五托拉斯的负责人互相勾结,把八万二千七百零五个卢布攫为己有。哈萨克斯坦江布尔瓜果国营农场场长和农场党组织书记,两人占了两公顷半宅旁园地,雇工经营果园,工资由国营农场开支,出售蔬菜所得的数千卢布,都落到他们两人的腰包里去了。
资产阶级特权阶层通过高工资、高稿酬、高奖金和贪污盗窃等种种手段,获取高额收入,过着奢侈的资产阶级生活。哈萨克建筑材料和构件联合公司的经理在很短的时间内,造了两层楼的“哥德式”私宅,“简直是贵族的宅第”。在哈萨克共和国,造别墅私宅成风,阿列克谢耶夫卡的“所有领导都有私宅”。亚美尼亚有个农庄主席占用农庄的建筑材料,剥削庄员们的劳动,给自已建造了一所高级别墅,房屋建筑面积六百十六平方米,庭院里有喷泉,四周有坚固的围墙,一切都很阔气,老远就看得见农庄主席这座三层楼房。上述的纪念伊里奇集体农庄主席,为庆祝自己再度当选,大宴宾客三百多人,一九七一年仅礼宾迎送就耗费农庄资金一万二千多卢布,还专门拍了一部电影“颂扬他这个集体农庄主席的活动”,农庄为这部电影开支了一万三千卢布。鞑靼自治共和国明泽林区图凯集体农庄有三辆小汽车和一辆带坐斗的摩托车,只准农庄主席一人使用,成了他的私人车队。
另外,分布在文化、教育、科技等部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阶级基础。这些高踞于劳动人民之上的精神贵族,也有极大的权势和特殊待遇。他们通过高工资、高稿酬以及种种额外收入,分到一部分剩余价值,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苏联科学院院士的每月固定工资为一千五百至二千卢布,加上挂名差事、稿费等,每月实际收入为三千卢布左右;大学教授月薪达二千五百卢布;电影演员月薪四百五十卢布,加上每月额外收入二千卢布,实际收入达二千四百五十卢布。此外,苏修统治集团每年还把剥削来的剩余价值,以颁发各种奖金为名,在这些精神贵族之间进行分配。一笔盗用列宁名字的奖金的金额就有一万卢布,一般的国家奖金也达五千卢布之多。据有关材料,莫斯科医学院院长年薪三万美元,加上开设私人诊所每年收入大约十万至二十万美元。一个心脏病专家,开设私人诊所,每年收入四十万美元。作家肖洛霍夫是一个拥有私人别墅、私人飞机,以及大量其他私人财产的大富翁。一个苏联著名芭蕾舞女演员,住着一幢十分富丽堂皇的建筑物,有花园和亭台,“华丽的磁砖浴室,简直象白宫里的浴室”。这些精神贵族也都享有从特种商店购得高档消费品和出国旅行等特殊权利,他们有一般群众不得问津的专设的俱乐部和游乐场所。
苏联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精神贵族,还建立一种变相的“世袭”制度。他们“许多人把依附于权力的各种好处传给了子女”,他们“按惯例可以把他们的子女安排到孩子们想去的任何地方去工作”,他们把大学作为子女走向新资产阶级地位的晋升阶梯。苏联的大学为这些特权阶层的子弟大开方便之门,据苏修“学者”透露的材料,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高等院校的全日制学生中,工农及其子女的比重,一九六四年为百分之五十九点六,到了一九六九年,已下降为百分之四十九点三。同时,函授部学生中农民及其子女的比重,也从一九五九年的百分之二十五点三,锐减到一九六九年的百分之零点六。
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构成了现今苏联资产阶级的主体。同它有着各种联系的,还有苏联社会上的其它资本主义势力。其中有在社会主义革命中被推翻的资本家、地主、富农、贵族、俄国将军和教会官员,据一九二八年统计,占当时苏联人口的百分之四点六,大约七百万人。三十年代以来没有这方面的统计数字发表,但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还是存在着,在苏修叛徒集团统治下,他们重新活跃起来。还有开设地下工厂、地下建筑公司和地下商店的新资本家,和雇工经营宅旁园地的新富农,以及在自由市场上从事投机贩卖的暴发户,他们主要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产物,现在成了新财主,同被推翻的旧剥削阶级一样,是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同盟军。此外,还有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贵族,主要是被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用高额奖金及各种优待(如分给较好住宅、公费旅行等)收买的某些所谓“劳动英雄”和“工人代表”。所有这些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总数不到苏联人口的百分之五,不到一千万人(西方估计为五百万到七百万人)。他们就是苏修叛徒集团的社会基础,也是今天苏联的“拥有权力的上流社会”。
与此相反,在苏修叛徒集团统治下,被压在社会最低层占苏联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则完全处于被奴役、被剥削的地位。他们早已不再是国家和企业的主人,广大劳动人民两手空空,只能靠出卖劳动力,过着日益贫困的生活。
根据苏联官方公布的材料,从一九六〇年到一九七三年,平均工资的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四,而同一时期内,所谓“国民经济货币积累”,即国营企业的利润和周转税,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八以上,其中利润的增长率约百分之十一点五。工人和职员所受的剥削加重了,他们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不断下降。必须指出,这个所谓平均工资,在计算中包括了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工资,从而大大夸大了一般工人的平均工资水平。事实上,一般工人的平均工资要比这低得多,而且工资提高的数额又被物价上涨所抵消。苏联职工绝大多数的工资水平在平均工资以下,半数以上的工人都是低工资。以列宁格勒机器制造业职工工资为例,一九七〇年工资水平在平均工资一百二十卢布以下的,在“非熟练体力劳动工作者”中间占百分之六十六点八,“中等熟练程度的非体力劳动工作者”中占百分之九十二点六,“在机器和机械操作场所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熟练工作者”中占百分之四十三点五,“主要从事体力手工劳动的熟练工作者”中占百分之二十九点六。后两类人员一般属工资级别较高的熟练工人,但也有近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人工资水平在平均工资以下。列宁格勒是个大城市,生活费用和工资水平多较高,机器制造业又是工资水平较高的部门。从全苏情况来看,工人和一般职员工资水平在平均工资以下的,比重就更大了。据苏联劳动科学研究所一九六七年材料,一户四口(两个在职的成年人和两个孩子)的标准家庭,维持必要的生活水平,平均每人每月需要五十一点四卢布。但是,苏联现在很多工人和一般职员的工资(包括奖金)收入仍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例如,列宁格勒机器制造业职工,一九七〇年初按家庭人口平均计算的收入每月在五十卢布以下的:“非熟练体力劳动工作者”中有百分之十三点七,“中等熟练程度非体力劳动工作者”中有百分之十八点六,“在机器和机械操作场所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熟练工作者”中有百分之十一点三,即使“主要从事体力手工劳动的熟练工作者”中也有百分之十四点三。这四类人员家庭每人平均收入在三十卢布以下者,分别有百分之二点一、一点一、零点八和零点八。现在苏联拿最低工资的工人占了工人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三以上,全苏工人家庭每人每月收入在五十一点四卢布以下的数量很大。苏联官方自己承认,需要对平均收入五十卢布以下的家庭给予救济的有二千五百万人,即占苏联人口的百分之十以上,约占全苏城市人口的五分之一。
在今日的苏联,如果工人和一般职员丧失了劳动能力,收入就更加可怜了。优抚金的最低额,直到一九七一年七月一日,才从三十卢布提高到四十五卢布。靠领优抚金过活的职工,一九七〇年初有四千万人,一九七二年初增至四千二百万人,一九七三年初达四千三百万人。由于靠非薄的优抚金无法维持生活,许多年老体弱已退休领优抚金的职工,被迫重新参加工作。据透露,“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一年领优抚金而继续参加工作的人数从百分之十四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一”。
苏联工人阶级贫困化和他们状况不断恶化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苏联现在经常存在着的大量“劳动力流动”现象。近几年来,“劳动力流动”已经达到了很大的规模。据苏联《接班人》杂志透露,过去儿年苏联工业和建筑业的流动人员每年达一千万人次,每人每次“流动”平均二十八天,这就是说,每年相当于有一百多万工人不工作或失业。加上其他部门的流动者,全苏每年大约有二百万人不工作或失业,“劳动力流动”的面相当普遍,一九七二年,工业企业工人流动达到平均在册人数的百分之十九点八。人数众多的“劳动力流动”,是苏修叛徒集团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把苏联变成了新型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必然现象。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为了最大限度利润而大规模裁减人员。例如,谢基诺化学联合企业到一九六九年一月止裁减的职工中,被辞退和送去当兵的就占百分之二十三,差不多每四个人中有一个人被踢出工厂,这些人中除了百分之四点七五的人当兵以外,大多数加入了流动劳动力的队伍。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五家汽车公司在改行“新体制”后,五个月内就解雇了二百三十九人。莫斯科第十五卡车维修厂的经理,为了赚更多利润,一次就解雇了全厂百分之十的工人。在苏联,法令规定企业领导人有权可以任意解雇工人。企业领导人“随便驱逐不合自己心意的人”,“无缘无故开除对自己提意见的人”,“什么东西都可以成为惩罚工人的理由”,从“诽谤领导人”,“不让人安宁地工作”,直至“违反婚姻法”,都可以被开除出厂。例如,亚美尼亚共和国第二有色金属局局长克罗皮扬解雇的人员:有的因为目光不怀好意,有的是因为不是他的亲家,有的则因为外孙需要这个职务。局里定额人员共为六十二名,而克罗皮扬坐上局长宝座十五个月以来,他先后招收和解雇的有七十九人。象这样随意解雇职工的事件,一九七〇年在阿塞拜疆共和国就占劳资解雇冲突事件的百分之六十。
苏联这种所谓“劳动力流动”,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产业后备军。马克思说过:“过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一支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它绝对地隶属于资本,就好象它是由资本出钱养大的一样。过剩的工人人口不受人口实际增长的限制,为不断变化的资本增殖需要创造出随时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苏修叛徒集团统治下的苏联就是这样,一方面,把成千成万不合他们需要的职工踢出工厂大门;另一方面,却在全国十万人以上的城市普遍设立了二百五十多个官方的劳动市场—“劳动就业局”或“职业介绍所”,为需要的企业招收廉价劳动力,并从中赚取佣金。工人阶级在苏修叛徒集团眼里仅仅是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奴隶。
农庄庄员同工人一样,受尽剥削和压迫,终年劳累,只换得微薄的“劳动报酬”。虽然按照苏联官方公布的材料,一九七二年农庄庄员的月平均报酬约为八十个卢布,但有许多农庄的月平均报酬要比这个水平低得多。例如,有一批农庄,每一劳动日的报酬还不到一个半卢布,如按全苏平均每月出工十八点八天计算,月平均报酬只有二十八卢布,远远低于当年平均数。在大田从事畜力手工作业的大量普通庄员,他们的报酬很低。按全苏集体农庄平均,一九六九年在大田从事畜力手工作业的庄员,全年收入只五百卢布左右,即每月约四十一卢布。有许多人的报酬实际上还达不到这个平均数。例如按当时的规定,国营农场从事畜力手工作业的工人最低一级工资是日工资一点七二卢布,根据这个标准按每月出工十八点八天(全苏平均数)计算,那么,集体农庄中从事畜力手工作业的庄员每月报酬只有三十二点三卢布。农庄中这部分庄员人数非常多,一般占农庄庄员人数的百分之五十四到七十。
农庄庄员按每一家庭人口平均计算的收入也很低。与工厂工人家庭相比,一九六三年为百分之五十八;与国民经济职工家庭相比,一九六九年为百分之六十九。庄员从社会消费基金得到的收入按每人平均计算,为职工的三分之一。庄员一九六七年以前,没有社会保险制度,以后虽然靠农庄提取社会保险基金才建立了这个制度,但标准很低。养老金的最低限额,一九七一年七月一日起,才从原来的每月十二卢布提高到二十卢布。因工伤或职业病造成残废的津贴每月最低限额一等为三十五卢布、二等二十五卢布、三等十六卢布。因一般疾病造成残废的津贴最低限额一等为三十卢布、二等为二十卢布。失去供养者的家属抚恤金每月最低限额,家有三个或三个以上无劳动能力者为三十卢布,家有两个无劳动能力者为二十卢布,家有一个无劳动能力者为十六卢布。这样低的养老金和抚恤金,根本难以维持个人的生活。
由于受不了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农庄庄员大量外流。据统计,一九六〇至一九七〇年农庄庄员人数减少了约一百八十万人(不包括因农庄改为国营农场而减少的庄员人数)。据苏联一刊物最近发表的数字,农村流入城市的人口,一九五九至一九七〇年间共达一千六百四十万人,平均每年达一百五十万人。近几年来,这一外流趋势有增无已,每年达到二百万人。大量人口外流,特别是青年大量流向城市,使“有劳动能力的集体农庄庄员大大衰老了”,“有的地方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平均年龄为五十岁”,“妇女在生产中担负大约三分之二不适当的劳动”。面对苏联农村这一片衰败景象,苏修头目叫嚷要增加“农村的吸引力”,“培养农民对土地的爱”。但是,现在的集体农庄既然已经不是苏联农民自己的农庄,这种声嘶力竭的狂叫,又有什么用处呢?
赫鲁晓夫一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统治二十多年来,苏联的广大工农群众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各族人民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统治集团的矛盾日益尖锐化。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十分害怕和仇视苏联工人及其他劳动人民。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四大反复强调“加强法制”,波德戈尔内也发表电视讲话,说严格遵守法律是每个人的“首要义务”。报刊叫嚷“法院、检察院、仲裁部门、公证组织、警察机关和其他行政机关应当更坚决地进行加强法制的工作”。他们千方百计要人们“绝对遵守”资本主义的剥削秩序。
今日的苏联,全国充满着法西斯的白色恐怖。只要谁对苏修统治集团的剥削和压迫流露不满,敢于斗争,谁就会被监视、钉梢、传讯,或送进“精神病院”,就会以“诽谤苏联国家和社会秩序”的罪名,被逮捕、流放。集中营、劳改营、监狱、“疯人院”遍布全苏。在苏联的上千个集中营中,关押了几十万政治犯。而受其他各种形式监禁的人数,更远远超过此数。
但是,血腥的统治和残暴的镇压,阻挡不住苏联人民的觉醒和日益增长的反抗。早在一九六二年就有诺沃切尔卡斯克城反对提高肉类和黄油价格的斗争;一九六三年敖德萨码头工人抗议食品涨价的罢工;一九六五年埃里温人民的斗争;一九六八年克里米亚鞑靼人在奇尔奇克城的游行示威;一九六七年奇姆肯特城的大暴动;一九六八年至一九六九年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橡胶制品厂举行的罢工;一九六八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附近的一个小镇霍罗尔发生矿工争取面包的斗争。到了七十年代,群众斗争进一步发展。例如,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五日,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发生了成万人参加的斗争,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也经常有罢工发生。
赫鲁晓夫一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还在各民族“接近”和“融合”的幌子下,对苏联境内少数民族实行帝国主义的殖民掠夺政策,迫使少数民族地区向单一经济畸形发展,把各少数民族地区变成了原料和农副产品供应地。残酷的民族压迫和殖民掠夺,激起了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毛主席:《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在苏联工人阶级斗争的推动下,各少数民族人民也掀起了反对苏修叛徒集团的斗争,尽管许多人以“民族主义”罪名,被关进监狱或苦役营,但少数民族人民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压迫和奴役的斗争,仍然此起彼伏。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现在,苏联各族人民日益觉醒,苏联人民反对苏修叛徒集团的群众斗争,正在向前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苏联人民终将推翻修正主义的统治,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