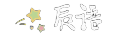暂无AI摘要
暂无AI摘要 路边社记者:莫大师,现在有个网友说要起诉你,你怎么看?
莫言:起诉我?这也太秃然了吧……

路边社记者:真的,那个网友自从你得了诺奖,就咬着你不放了。
莫言:哦,狗还在咬,说明我写的还行。
对不起,侮辱狗了。
喂狗三日, 它记住你三年;
善待人三年 ,一天就能忘记你。
狗永远是狗,但人不一定是人。
路边社记者:那你怎么都不回应呢?
莫言:狗要吃屎,你千万不要制止,不然它以为你要跟它抢,说不定还会咬你一口。
路边社记者:作为一个作家,这是不是对人性想的太负能量,太黑暗了呀?
莫言:所谓的人性,就是在无权无势善良的人身上挑毛病,然后在道德败坏有权有势的人身上找优点。
路边社记者:这……做人还是要善良的吧?
莫言:不管你多么善良,当你没有价值时,就算你温柔得像只猫,别人都嫌你掉毛。
路边社记者:额……那请莫大师开示,到底要怎么做人呢?
莫言:做人很简单。
人饿了,别吃葱,烧心;
人穷了,别走亲,寒心;
不疼你的人,不要去找;
不帮你的人,别去讨好;
不想你的人,绝不打扰。

路边社记者:咳咳……聊岔了,再说这个起诉你的网友,也有网友说他是拿“爱国”当灵活就业了,你怎么看?
莫言:我用眼睛看。
路边社记者:额……对此你就没有想法跟读者分享吗?
莫言:那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从前有一只天鹅,不幸掉进了乌鸦窝里,然后处处被排挤,受尽苦难,
后来才明白原来问题出在自己洁白的羽毛上,于是它就去焗油了。
在乌鸦的世界,最不能容纳的就是洁白,它们会从仰视到轻蔑,再到狠狠践踏。
当浑浊成为一种常态,清白便是一种罪过。
真正可怕的坏人,是那些不知道自己坏,反而认为自己正确,认为自己很好的人,他们没有良心,却挥舞着良心的大棒打人,他们没有道德,却始终占据着道德高地。
路边社记者:您的意思是,做人要合群,随大流吗?
莫言:合什么群,合谁的群,和谁合群!你总关心别人怎么看你,但狼从来不理会一只羊的意见。
路边社记者:额……我又分裂了。那做人到底是要合群,还是要做自我啊?
莫言:那我再给你讲个故事。
从前有个人,他总说要战胜自我,终于有一天,他战胜了自我,那么请问,他是赢了?还是输了?
路边社记者彻底崩溃,拿头撞墙,许久才缓缓的吐出一句话:不愧是诺奖大师,太深奥了,我真不懂,我真懵逼了。
莫言:每个人都有一个死角,自己走不出来,别人也闯不进去。
我把最深沉的秘密放在那里。
你不懂我,我不怪你。

路边社记者:额……那您能跟读者讲讲您是一个怎样的人吗?
莫言:慢热,沉默,喜欢独处。
不记仇,健忘体质,比你想象的深情,也比你以为的冷漠。
路边社记者:额……大师果然是大师,用词不拘一格,用深情对仗冷漠……对了,这就是您要对读者分享的爱情观吗?
莫言说:爱情很简单。
男人好色,人的本性。
女人上半身是诱惑,下半身是陷阱。
男人上半身是修养,下半身是本质。
十男九好色,无关人品,程度不同。
有七情六欲的是人,没七情六欲的是物,能够掌控七情六欲的那才是人物。
路边社记者:额……那人生观?
莫言:人生很简单。0岁出场,
10岁最废物的年纪却得到了最多的夸奖,
20岁为情彷徨,
30—-40岁基本定向,最需要打气的年纪却肩负了最多的承担,
60岁告老还乡,搓搓麻将,晒晒太阳,
80岁挂在墙上,正所谓生的伟大,去的凄凉。
人品越好,朋友越少;
人越踏实,混得越差;
心越善良,苦难越多;
做得越对,活得越累。
……
眼看莫大师正要滔滔不绝个没完,路边社记者赶紧截断了话头:额……人真的是心越善良,苦难越多吗?
莫言:世事往往如此,当一碗水端不平的时候,只有牺牲那个最善良的,才能风平浪静。
一旦那个善良的不愿意再牺牲了,就会被扣上一个破坏和睦的帽子。
路边社记者:额……这就是你为什么不回应那位网友,或者说取这个笔名的原因吗?
莫言:你不懂我的突然沉默,又怎么会懂我不想说的难过。
路边社记者:额……感觉又被您给绕回来了。
求求您了大师,你就说点什么吧,我回去不好交代。
莫言:那我再给你讲个故事吧,从前有一只天鹅……
路边社记者:大师你……
莫言:咳咳,记岔了。
你还记得当年在菜市口处决戊戌六君子时,那观刑的人山人海吗?
跟现在的网络很像,
我相信那人山人海里,大多也是可以用善良来定义的百姓,
但那些刽子手,之所以要那样夸张地表演,就是为了满足这些善良的看客的需要。
而那些受刑人,之所以能够那样慷慨悲歌,视死如归,其中也有为了看客而表演的成分。
这就是网络,或者说广场的精髓:极端才有流量。
在极端流量的裹挟中,看客在等待阴暗,等待污点,等待倒下,等待坍塌。
于是会有侩子手专门制造阴暗,寻找污点,制造倒下,制造坍塌。
于是乎,有多少善良的百姓,变成了残酷的帮凶。
问题不在我的看法,问题甚至跟我无关。
问题从来都是,
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