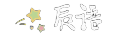暂无AI摘要
暂无AI摘要 
“马克思遇到孔夫子”似乎一时风头无两,各路学者极力佐证,马克思与孔夫子乃是一个共通的结构,最终的目的当然是试图佐证,马克思主义进入到中国,不是偶然的,乃是历史的必然。
于是在这里,我们不仅仅是“人民的选择”,也不仅仅是“历史的选择”,并且还是“传统文化的选择”,故而我们的“必然性”似乎是更加强烈了。
所以湖南卫视趁热打铁,推出了所谓的《当马克思遇到孔夫子》讨论,两者的相似性,以及两者的结合性。
所以就这个问题,我们来深入讨论一下,马克思真的能够遇到孔夫子吗?
各路学者论证的方法,方式以及结论,是否可靠呢?在这篇文章,我们系统地检讨一下,各路学者的讨论的问题所在。
1、问题源头
对于所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其实早在八十年代就有人开始讨论。
但是如果我们翻阅相关的论著文献,我们会发现,把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互结合起来看待,最开始的文献资料,都不是为了佐证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的必然性。他们的隐藏的论证目的,恰恰是试图否认马克思主义一元论文化观。换言之,最开始佐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关系,其实是持有一种批判立场的学者所做的研究,他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研究呢?目的就是为了检讨,所谓“救亡与启蒙”的关系。
在八十年代的时候,李泽厚就曾经对此研究过,他曾经发出这样的感慨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性品格非常符合中国人民救国救民的需要。但是,中国传统的民族性格、文化精神和实用理性是否也起了某种作用呢?重行动而富于历史意识,无宗教信仰却有治平理想,有清醒理知又充满人际热情······这种传统精神和文化心理结构,是否在气质性格、思维习惯和行为模式上,使中国人比较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呢?①
但是李泽厚发出这样的感慨,绝非是为了论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有什么必然性的关系。
后来包遵信曾经研究说:
这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似乎还找不到,倒与中国儒家传统有着内在一致的关系。把思想文化完全意识形态化,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政治伦理原则制约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政治伦理价值取向成为支配人的一切活动的主导原则。这就是儒家伦理本位主义的基本特征。
后来金观涛研究说:
从结构上讲,当代中国大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既不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包括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也不是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一种用马克思主义语言表达的,但结构上十分类似于儒家文化的思想系统。因此,才会出现当代中国文化史上最奇特的现象:表面上是用马克思主义彻底的批判旧文化,但这种运动又必然是顺着儒家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展开的。因此,一方面传统在名义上遭到批判,另一方面与其等价的东西却在运动中制造出来,而且在现代的名义下变得出奇的强大。
可以看到,这些前面的研究者,无一例外都是体制之外的人,或者说他们的研究目的,在事实层面上,是强调两者之间存在着某些相似性。但是论证的目的,却不是为了论证所谓“中国文化的选择”。
与这种研究相似的,是另外一种研究。这种研究试图去把握,所谓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潮与他本国,例如说自由主义与基督教的关系,目的在于检讨中国何以无法形成自由主义。
这样的研究,其理论背景和方法都是一样的,区别仅仅在于研究的目的不同。
包括新儒家的牟宗三,试图去论证康德与中国儒家的相似性,其实其论证手法也是相似的,目的也是相似的。
2、文化形态说与文化进化论
对于“文化”,历来有两种看法,一种持有一元论的思潮,一种持有形态论的思潮。
所谓一元论,看待文化的视角,乃是“古今之变”,在这个视角中,文化是有高低贵贱之分的,而这样的高低贵贱,乃是基于所谓“启蒙”的立场上形成的。
在康德,谢林,黑格尔,马克思等人那里,整个人类历史被整合为一个自我意识成长的系统,这个系统表达为,从最开始懵懵懂懂的束缚在必然性之中,随后逐步扩展为整个自我意识的觉醒,个体性的觉醒,最终实现个体性和普遍性的统一,所谓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绝对精神”云云,其目的都是一样,都是试图去整合近代个体性张扬与共同体整合之间的矛盾。
而根据这个系统,就会依照精神的觉醒程度不同,进行排列。所以黑格尔谴责中国说,中国属于历史的开端,却是最懵懵懂懂的,孔子是压根没啥哲学的。中国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等等,都是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中完成的。
而马克思同样是这种一元论的信奉者,马克思曾经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以及著名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说:
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我们不应该忘记那种不开化的人的利己性,他们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静静地看着整个帝国的崩溃、各种难以形容的残暴行为和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杀,就像观看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衷;至于他们自己,只要某个侵略者肯来照顾他们一下,他们就成为这个侵略者的无可奈何的俘虏。我们不应该忘记:这种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的生活方式,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甚至使惨杀在印度斯坦成了宗教仪式。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小小的公社身上带着种姓划分和奴隶制度的标记;它们使人屈服于环境,而不是把人提升为环境的主宰;它们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况变成了一成不变的由自然预定的命运,因而造成了野蛮的崇拜自然的迷信,身为自然主宰的人竟然向猴子哈努曼和牡牛撒巴拉[注:哈努曼是印度传说中的神猴,后来被奉为印度教的毗湿奴的化身。撒巴拉是神牛,在印度教中被奉为财富和土地之神。——译者注]虔诚地叩拜,从这个事实就可以看出这种迷信是多么糟践人了。
这段话,鲜明地表达了马克思的文化观点,即他信奉一种启蒙思潮建立起来的一元论,以及历史进步论观点,他把印度的公社生存,理解为东方专制主义的基石,不管看起来多么无害,他们都不是精神的选民。在这个意义上,虽然马克思并不鼓吹所谓殖民者的殖民,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殖民活动使得野蛮变成了文明。
而恩格斯也是一样,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赤裸裸地说:
奴隶处在竞争之外,无产者处在竞争之中,并且亲身感受到竞争的一切波动。奴隶被看作物,不被看作市民社会的成员。无产者被承认是人,是市民社会的成员。因此奴隶能够比无产者生活得好些,但无产者属于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他们本身处于比奴隶更高的阶段。
这话与所谓被嘲笑的“你们丧失了一切,但是你们毕竟获得了自由”,其实意思并没有什么区别。
在恩格斯和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失去了一切,但是无产阶级却成为历史的使命承担者,原因就在于他们获得了“自由”。
与这种一元论文化观相反,还存在着一种文化观,叫做"文化形态说",这种观点肇事于歌德,开创于斯宾格勒,后来的亨廷顿、汤因比都是这种文化观。这种文化观,否定所谓一元论的观点,而是把各个民族的文化,视为一种有机体,他们各自是独立的。严格说来,他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于是“文化”就作为一种大杂烩,涵盖了一个民族的一切,在亨廷顿那里,就表达为所谓文明的冲突。
而所谓的文明的冲突的视角,不再是冷战时期的两种意识形态。在苏联和美国抗争,他们的意识形态之争,实际上是古今之争。苏联谴责美国是资本主义,是落后。而自居自己是更高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义。所以苏联文化是更胜一筹的。
而在亨廷顿那里,文明冲突意味着各种文明相互平等,他们的冲突不再是意识形态的冲突。而这样的视角,一定程度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一元论思想观。
并且伴随着斯宾格勒,亨廷顿,在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显然有着一种“思想启蒙和解放”的意义,他让我们看到文明的多样性,从那种一元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也正因为如此,八十年代的河殇之争,中化还是西化之争,保守和激进之争,他们的视角都不再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一元论世界观,而转化为各种文化的争端。
换言之,问题不再是“古今之变”,而成为了“中西之别”。这样的视角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是有解放意义。
但是他的弊端是显然的,首先在于
1、模糊制度和文化之变。譬如说亨廷顿把中国视为儒家文明,与西方基督教文明进行斗争。而这样的论断,在何种意义上是成立的呢?中国是儒家文明?今天的中国,何有一丝一毫的儒家的影子呢?亨廷顿本人乃是一种保守主义者,他有这样的观点并不稀奇。
但是中国学人之所以亦步亦趋地照搬,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害怕“Culture revolution”的来临,他们把这样的活动,视为是所谓“激进西化”的问题。
应当说这样的判断,在一定程度上有道理的,马克思主义在各个国家,都是被作为典型的西化思潮而被接受的,但是显然把问题仅仅理解为中西之别,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保守主义”的立论基础,但是却抽干了自己的理论基地。即自由主义者要什么?难道不是一种制度吗?
如果把问题仅仅模糊为文化,就会陷入这样的泥潭,即自由主义者无法提出积极性的论断,因为中国文化显然与西方文化不同。自由主义者一开始就是启蒙思潮的一部分,他就分有了启蒙的普遍性,离开了这样的普遍性,片面地强调所谓特殊性,其结果就变成了“秋风”式的复古。
2、就是这样的文化分别,会容易倒退为另一种模式。我们知道,自由主义者最先提出这种文化形态的观点,而这样文化形态的提出,一方面是检讨何以“救亡压倒启蒙”,但是在事实判断上,却有一个功能,恰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相似性,从而缔造一种新的历史神话,即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人民的选择,不仅仅是历史选择,竟然还是”孔夫子的选择“。
孔夫子在九泉之下,会如何想这样的问题呢?
3、马克思能够遇见孔夫子吗?
那么,我们就应该正面去问这个问题,马克思能够遇到孔夫子吗?
山东大学的何中华先生,就以《马克思与孔夫子》为题目写了本书

其目的你想要论证,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乃是”孔夫子的选择“。
首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引用,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列宁的老师普列汉诺夫的一句话作为题眼
“特殊论”是停滞和反动的同义词,俄国的进步力量都凝聚在西欧主义的大旗下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就存在着所谓民粹社会主义,所谓民粹社会主义,就是坚信俄国的特殊论,他们认为,俄国是特殊的,所以俄国并不需要经历资本主义,就可以变成了社会主义。
但是在普列汉诺夫和早期列宁那里(甚至是晚期列宁),无一例外都在批判这样的特殊论调。
因为马克思主义一个基本的论断就是,无产阶级革命乃是全球性,乃是阶级性,而非单个民族,单个文化的产物,无产阶级革命植根于工业大生产,而工业大生产乃是植根于资本主义在全球性的扩张。所以无产阶级革命,必然带着普遍性,而绝不是单纯的特殊性。
所以,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坚决地与这种特殊性论调做斗争,反对民粹主义强调本国特殊的论调。
与此相对,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一例外也对这样的特殊性进行斗争,例如说郭沫若,就曾经批驳所谓中国特殊论,他之所以批驳这样的观点,显然与当时试图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合法化有关。
我们不能一味地强调特殊性,也不能一味地强调普遍性,这是很自然。但是问题并不在于这样的”片汤话“,而在于,马克思主义真的与所谓儒家思想,或者任何一家思想,有本质性的相似性吗?
我们可以说,并没有。他们的确有相似性,但是这样的相似性,绝不是这些学者”水论文“所说的论据,我们下面来谈论这样的本质性和相似性。
首先是,两者具有本质性的不同。马克思主义属于社会主义这一类,但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的范畴之下,有很多类型,在《宣言》中,马克思就批驳了很多其他所谓社会主义的观点。
所以,知道这一点,这些学者所提出的一些论点,都是站不住脚,这些论点包括如下:(不完全列举)
1、大同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把两者的等同起来,并且写成论文,简直是侮辱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名号。因为但凡了解社会主义历史都会知道,强调所谓”大同“,根本不是中国所独有,在西方无论是理想国,还是基督教公社社会主义思潮,无一例外都存在相似的思想。
但是我们能够说,马克思主义与这些社会主义是一样的吗?马克思主义与这些社会主义有一个本质性的不同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相信”异化和扬弃异化的道路是同一条路“,即他相信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情况下,正如我们喜欢引用的一段话,马克思说:
自然,任何人都没有我们这样不喜欢资产阶级统治。当洋洋得意的当代“办事人物”[注: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把共产主义者称为“冷酷的理论家”,而把自己叫做“办事人物”。——译者注]把时间浪费在无谓的争吵上的时候,我们就在德国首先提出了反对资产阶级的主张。
但是我们向工人和小资产者说:宁肯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里受苦,也不要回到已经过时了的旧社会去!因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以自己的工业为建立一种使你们都能获得解放的新社会创造物质资料,而旧社会则以拯救你们的阶级为借口把整个民族抛回到中世纪的野蛮状态中去!
在当时,也存在着一种寄希望一种田园牧歌式的模式,例如说蒲鲁东。但是马克思主义显然是反对蒲鲁东主义的。而中国的大同社会是一种纯粹的复古。
并且且不用复古还是进步这样的观点,洪秀全、孙中山无不试图引用这段话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但是我们可以说,这段话可以必然地为他们的观点服务吗?如果可以的,岂不是中国的未来道路是洪秀全的社会,还是孙中山的社会。
2、辩证法的强调。
很多人认为中国古代就有辩证思维,所以他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相似的。这样的比附是荒唐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继承黑格尔的辩证法。而黑格尔早就对此有解释,他说在原始时代,由于没有知性思维,人们通过感性的时候,会略微地意识到一种辩证思维。但是这样的辩证,完全不触及概念。
后来的法国人类学家布留尔,提出了互渗律,认为原始人类还没有主客之别,陷入到了一种互渗的状态,是一种泛灵论,在精神谱系中,其实是最低端的状态。
所以把中国的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比附,完全是一种不懂辩证法的举动。至于中国的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邓晓芒曾经做过一个解释。西方的辩证法核心在于自否定,强调的是自由,而绝不是中国把两个相反的范畴结合在一起,这样的辩证法实际上不是所谓辩证法。
3、天人合一和所谓主客统一。
很多学者说,马克思主义否认主客分裂,强调统一。与中国式的天人合一是相似的。这样的比附也是失败的,因为马克思的老师黑格尔早就对此进行了解释,中国的天人合一没有个体性因素,没有极端的主观性因素,还是实体性。他只是表面上显露出相似的状态,实际上两者本质上是不同的。
还有一种论证,以海德格尔为中介,因为海德格尔赞赏中国的道家,一些研究马克思的学者,把马克思首先海德格尔化,然后又以此与中国道家相关,又通过儒道佛三家合一统一起来,从而论证马克思与儒家的关系。
这样的比附,依然是失败的。并且把海德格尔与中国文化联系起来,是彻头彻尾的无知表现。因为海德格尔强调”本有“不是中国式的”道“,本有依然强调的是此-在,跃入无之中,这样的跃入仍然是主体性的表达,这样的表达与中国式的天人合一,完全不同。
4、实践导向
以实践导向作为论断,也是失败的。因为宗教的特质就是强调实践,例如说佛教的十二无计。由此强调实践,根本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只不过是宗教演变的产物。相反纯粹理论的探讨才是特殊的东西
那么这些不同,是否有相似之处呢?这个相似之处就在于,德国文化在现代化中的位置是相似的。我节选一部分论文,


换言之,他们在反对西方,强调所谓“超克现代性”这一点有相似性。
并且一个事实是,中国的儒家,实际上是小共同体本位的思潮,这种思潮是带着等级性提供出来的,他与一种强调普遍性的思潮本来就是不相容的。但是中国的儒家,又具有轴心文明都具有的普遍性的特征。所以两者又有普遍性的重叠。但是这样的重叠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各个轴心文明都强调一种普遍性,这说明不了什么。
总之,用恩格斯的一段话来说,
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
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是启蒙运动的产物,他虽然批判现代社会,但是归根到底他却是启蒙的继承者。而离开了这一点的理论,都是阉割性的。也正因为,马克思在《宣言》中说
于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就得到了一个好机会,把社会主义的要求同政治运动对立起来,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肆宣扬,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群众非但一无所得,反而会失去一切。德国的社会主义恰好忘记了,法国的批判(德国的社会主义是这种批判的可怜的回声)是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而这一切前提当时在德国正是尚待争取的。
[1]顾乃忠.三论维特根斯坦的文化观——如何看待维特根斯坦批评西方文化[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1(06):34-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