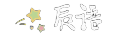暂无AI摘要
暂无AI摘要 一位朋友翻译的论文,很不错。很好地批判了主流观点,刚好最近找了一圈基本都是主流观点的复读。并且较为全面地阐述了去集体化的影响,最后重新科学评估和计算了统计数据。
此书我已经上传zlib上了,感兴趣可以看看。由于zlib上传后需要等一天左右,因此可以先将此书加到收藏夹里,方便查找。
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农村去集体化与贫困:对主流观点的批判
彭肇昌(ZHAOCHANG PENG)
献给中国及全世界的劳动人民
摘要
本博士论文研究了中国农村去集体化(1978-1984年)的后果,这是一项对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System)取代毛泽东时代集体经济的根本性制度变革,及其对中国农村贫困状况的影响的研究。
论文首先考察了去集体化如何重塑了中国农村经济中的生产、交换和分配领域,并发现其对中国农村的减贫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随后,作者对官方的农村贫困统计数据进行了批判性评估,并重新估算了1978年后中国农村的减贫绩效。结果表明,自去集体化以来,中国农村的贫困状况可能没有得到大幅改善,甚至更糟的是,很可能有所加剧。
本博士论文提出的研究结果挑战了主流观点,即认为去集体化对中国农村减贫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看法。本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贫困研究具有启示意义:那些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看似行之有效的制度变革,可能并不利于推动减贫。
第一章 引言
本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去集体化运动(1978-1984年)在经济改革时期对中国农村贫困的影响。本论文分为四个章节。
第一章是引言章节。本章在现有文献的背景下阐述了本博士论文的主题,并阐明了在接下来两章中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和关键概念。
第二章和第三章构成本博士论文的分析核心,分别侧重于原因(即去集体化)和结果(即农村贫困)。它们共同揭示了自1978年以来,去集体化是如何塑造中国农村贫困状况的。
第二章聚焦于原因,即农村去集体化,并考察了中国农村经济制度中的这一根本性变革对其农村贫困产生影响的渠道。从方法论上讲,本章采用历史的、定性的方法,必要时辅以案例研究和定量数据。
第三章聚焦于结果,即农村贫困,并在对官方数据偏差进行批判性分析和校正的基础上,考虑到去集体化对农村贫困线的上行压力,提出了一套1978-2007年间中国农村减贫的替代性数据。从方法论上讲,本章采用定量方法,广泛使用描述性统计。
第四章是结论章节。本章总结了本研究的主要发现,并讨论了其对相关社会科学研究的启示。
1.1主题
本博士论文关注的主题是减贫。指导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在何种条件下减贫会得到促进或阻碍。1978年后的中国经验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潜在的绝佳案例。
近年来,中国政府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等国际组织,以及世界各地的主流学术界和媒体,普遍将1978年后的中国描绘成大幅减少农村贫困的成功案例。与此同时,中国也以其持续的市场化经济改革和快速的经济增长给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是中国实现显著农村减贫的原因,这几乎已成为一种主流观点。
然而,仔细审视后会发现,现有学术文献中并没有明确的研究来阐释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为何以及如何导致中国农村贫困状况显著改善。因此,尽管人们普遍相信这一主流观点,但任何关于中国经济改革和增长过程在减少中国农村贫困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结论仍有待证实。
本博士论文旨在通过聚焦中国1978年后经济改革的核心支柱——农村去集体化——对中国农村贫困的影响,来弥补现有文献中的这一空白。农村去集体化运动发生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初始阶段。事实上,它是整个改革进程的起点。它从根本上改变了管辖中国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并对中国农村经济及其他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考察农村去集体化对中国农村贫困的后果,将为理解中国经济改革及伴随的持续快速经济增长如何影响中国农村贫困提供一个批判性的视角。
在接下来的两个小节中,将对与本博士论文主题相关的现有研究进行文献综述,以便更清晰地展示本博士论文研究在相关学术著作中的定位,以及其基本关注点、主要目的和指导视角。本文献综述分为两部分,分别关于贫困研究和去集体化研究。
1.1.1 贫困研究文献
现有贫困研究文献中有两类与本博士论文研究项目相关。第一类关注经济增长对贫困的影响。第二类关注中国农村的贫困状况。
1.1.1.1 增长与贫困
由于提高国民收入对贫困人口生活水平的显着重要性,关于经济增长对贫困影响的文献十分丰富。在这方面,有两组研究值得特别关注。第一组试图确定经济增长与贫困之间或多或少普遍的因果关系。第二组则阐明了在实施经济改革的国有社会主义国家背景下,某些特定的经济增长过程对普通劳动人民生计的后果。
关于经济增长对贫困的因果影响,广义上讲存在两种相互竞争的观点。一种可称为“涓滴效应”观点。另一种可称为“贫困化增长”观点。
“涓滴效应”观点认为,经济增长可能会导致贫富收入差距扩大,但穷人的状况仍将改善,因为更高产出和人均收入带来的部分惠益将“涓滴”至穷人。在这一观点内部,可以区分出强硬论点和温和论点。强硬论点,常被错误地归功于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库兹涅茨 1955),认为经济增长不仅能减少贫困,而且迟早会缩小不平等。库兹涅茨研究了发达经济体的工业化经验,提出了倒U形“库兹涅茨曲线”,表明经济增长的初始阶段通常伴随着收入分配不均的加剧,但在某个临界点之后,经济增长将伴随着收入分配的均等化。值得注意的是,库兹涅茨本人并未打算通过这项计量经济学研究来推断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任何确定性因果关系。但相信“涓滴效应”观点的人倾向于将其经济增长最终会减少收入不平等的论点与库兹涅茨的开创性工作联系起来。
温和论点则关注在经济增长导致分配不均等时,穷人据称获得的绝对收益。与强硬论点相比,温和论点放弃了最终会实现均等化经济增长这一更具限制性的论点(多拉尔(Dollar)和克雷(Kraay)2002;萨克斯(Sachs)2005)。无论其强硬版本和温和版本之间存在何种内部分歧,“涓滴效应”观点都强调经济增长将为包括穷人在内的每个人带来绝对收益,从而减少贫困。多拉尔和克雷通过将其2002年文章命名为“增长对穷人有益”完美地总结了这一方法。
相反,“贫困化增长”观点认为,分配不均的增长可能会演变成贫困化增长,在此情况下穷人将遭受绝对损失。“贫困化增长”一词最初由贾格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巴格瓦蒂 1958)在不同背景下创造,指的是由于贸易条件恶化导致产出增长引起的收入下降。该术语后来被伊恩·利特尔(Ian Little)(利特尔 1976)、吉姆·博伊斯(博伊斯 1993)和瓦姆西·瓦库拉巴拉南(Vamsi Vakulabharanam)(瓦库拉巴拉南 2004)用来指代一种更普遍的情况,即穷人在经济增长中境况恶化。值得注意的是,就经济增长使穷人境况恶化而言,“贫困化增长”观点的开创性工作最早可以追溯到基思·格里芬(Keith Griffin)(及阿齐兹·汗(Azizur Khan))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进行的研究(格里芬 1965, 1974;格里芬与汗 1972, 1977)。在这一系列关于巴基斯坦(Pakistan)和亚洲(Asia)其他地区的研究中,格里芬(和汗)评论了在这些国家背景下经济增长未能转化为穷人福祉改善的失败,并将此失败归因于由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权力不平衡造成的不当制度和政策。
“涓滴效应”和“贫困化增长”观点之间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增长与贫困关系的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相关关系,即经济增长是否可能伴随着强烈的两极分化,从而使穷人的境况恶化。在这方面,“涓滴效应”观点通常严重依赖采用大型跨国面板数据集在一定时期内的统计分析,以便在宏观尺度上识别增长与贫困之间的相关性,这可能会稀释那些在经济增长下穷人变得更穷的具有理论意义的案例,并忽略面板数据所取自的时代具有历史偶然性和制度特定性的结构。而“贫困化增长”观点通常通过进行案例研究,采用与所研究特定案例相关的定量和定性数据,来识别在经济增长下穷人变得更穷的事实。通过运用这种方法,格里芬、博伊斯和瓦库拉巴拉南得以揭示在巴基斯坦、菲律宾(Philippines)、印度(India)及亚洲其他发展中地区存在的贫困化增长事实。
争论的第二个方面涉及增长与贫困之间的因果关系,即对于“涓滴效应”观点而言,解释为什么经济增长必然会将绝对收益涓滴给穷人;或者对于“贫困化增长”观点而言,解释为什么经济增长可能使穷人更穷。依赖其统计方法和相关性分析,“涓滴效应”观点通常未能就经济增长为何必然导致穷人绝对收益增加提出令人信服的理论解释,除了假设经济增长与减贫之间存在自动联系。相反,“贫困化增长”方法利用其案例研究方法和对增长动态的定性研究来表明,当所研究的特定经济增长过程中内嵌了导致贫困的收入分配因素时,贫困加剧或强烈的两极分化将会随之而来。例如,吉姆·博伊斯(博伊斯 1993)逐步分析了菲律宾在马科斯(Marcos)时代由绿色革命激活的经济增长如何一方面促使土地精英和商业精英致富,另一方面又导致稻耕劳动者贫困化。
有一项特殊的研究工作介于“涓滴效应”和“贫困化增长”研究之间。弗朗索瓦·布吉尼翁(Francois Bourguignon)基于一个包含约50个国家114个时段的样本,研究了减贫的增长弹性(布吉尼翁 2003)。其工作的理论结论包括:收入不平等水平是减贫增长弹性的重要决定因素,并且收入分配的变化在影响减贫结果方面发挥着重要且独立的作用。在检验前述样本中的经验数据时,布吉尼翁发现了一些经济增长伴随着贫困加剧的案例。值得注意的是布吉尼翁2003年的研究在处理增长和贫困数据时采用了通常由“涓滴效应”观点所使用的正规量化方法,但其得出的结论却是通常由“贫困化增长”观点所例证的。
关于国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对大众生计的后果,一些研究尽管不直接涉及农村贫困本身,但对本博士论文研究具有重要启示。
国家及其所采纳经济政策的阶级性质是所有这些研究共同关注的焦点。大卫·科茨(David Kotz)深入考察了1991年苏联国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并得出结论:苏联党-国官僚精英决心通过以市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取代现有的计划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来增进自身的经济利益,尽管这损害了普通劳动人民的经济利益并遭到了他们的反对(科茨 1997)。鉴于在国有社会主义的苏联和中国普遍存在的经济体制(基于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中央计划经济)的相似性,探究类似的逻辑是否可能适用于中国国家及其在某一历史关头的经济政策的阶级性质,将是明智的。
其他专门针对中国在这一方向上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早在1978年中期,即中国经济改革开始前夕,夏尔·贝特兰(Charles Bettelheim)基于对毛泽东逝世后两年内中国发生变化的考察,对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国家所代表的阶级利益进行了富有洞察力的分析(贝特兰 1978)。他的结论是,中国已经走上了以牺牲普通工农经济利益为代价恢复市场资本主义的道路。
一些近期对中国经济改革进程及其对中国劳动大众影响的研究证实了贝特兰的预测。马丁·哈特-兰兹伯格(Martin Hart-Landsberg)和保罗·伯克特(Paul Burkett)仔细记录了中国1978年后改革所产生的经济变化,重点关注了正在形成的新经济体系的市场资本主义性质以及这一新体系的内在矛盾。对工人和农民经济利益的损害是作者所分析的改革和经济增长过程的一个突出结果(哈特-兰兹伯格与伯克特 2004)。另一份有价值的报告由戴尔·温(D. Wen)撰写。她论述了1978年后经济改革对普通工农生计一些基本方面的影响,并得出结论,改革及其产生的经济增长是以牺牲多数人为代价来使少数人致富的(D. Wen 2005)。
尽管这些关于国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阶级性质的研究并未将贫困概念作为统计测量的量化指标来处理,但它们对最初的国有社会主义国家中与改革和经济增长过程相关的成本与收益不平等分配的理论和实证分析,确实做出了两方面贡献。首先,它们揭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即如果普通劳动人民(包括穷人)的经济状况曾经恶化,那也一点不奇怪,因为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决策的官僚精英们在开始经济改革时考虑的是自身利益,这些利益充其量独立于劳动大众的经济利益,最坏的情况则是与后者相冲突。其次,它们对经济改革和增长过程的不同方面如何以不同方式影响劳动大众的生计,提供了丰富而详细的讨论。这些为本博士论文分析去集体化塑造中国农村贫困状况的影响渠道提供了有益的基础。
总而言之,现有文献中关于经济增长如何影响减贫存在争论。“涓滴效应”文献认为增长减少贫困,而“贫困化增长”文献则认为在特定情况下增长很可能加剧贫困。关于国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后果的文献表明,1978年后中国穷人的状况可能已经恶化。在这方面,该文献可被视为“贫困化增长”观点在国有社会主义背景下的应用。但由于关于国有社会主义的文献缺乏对贫困概念的明确和量化处理,中国1978年后的经济改革,特别是其农村去集体化这一开端,是否确实导致了农村贫困的恶化,仍有待检验。
1.1.1.2 中国农村贫困状况
贫困研究文献中的另一组侧重于中国农村的贫困状况,而不必探究其背后的驱动力。根据所采用的方法论,该文献有定量和定性两种变体。
定量变体关注农村贫困的精确衡量,通常利用大规模调查数据。与“涓滴效应”观点和“贫困化增长”观点在增长与贫困因果关系上的争论非常相似,这种定量文献在中国农村贫困程度上也存在分歧。
关于中国农村贫困状况的主流观点是由官方统计数据塑造的,这些数据由中国国家统计局(Chines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以下简称NBS)以及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等国际组织提供和解读。
国家统计局声称,自1978年以来,中国农村贫困不仅大幅减少,而且中国剩余的农村贫困发生率非常低(中国国家统计局 1985-2010)。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同意1978年后中国农村的减贫成就显著,但如果遵循更严格的国际贫困线标准,如每日一或二美元,中国农村贫困的发生率仍然相当高(世界银行 1992, 2000, 2008, 2009;以及拉瓦雷(Ravallion)和陈(Chen) 2007)。
上述世界银行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分歧是次要的,因为遵循不同的贫困标准(每日一或二美元的国际标准,或中国政府制定的某一国家标准)肯定会产生对当前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的不同估计结果。事实上,中国政府和世界银行的主要结论是一致的,即自1978年以来中国农村贫困已显著减少。
一个重要的不同声音来自一个半独立的国际贫困专家团队,他们组织了一个名为中国家庭收入调查项目(China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以下简称CHIP)的项目。领导该项目的学者包括卡尔·里斯金(Carl Riskin)和阿齐兹·汗等国际经济学家,以及隶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简称CASS)经济研究所的赵人伟(Zhao Renwei)和李实(Li Shi)等中国经济学家。该项目下实施的调查是一项持续性调查,自1988年以来每七年进行一次。CHIP项目调查团队与中国政府国家统计局的工作人员紧密合作,因为调查样本户和地方支持人员均取自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队可支配的资源。然而,CHIP项目调查本身的设计和解读确实有别于中国官方的农村住户调查,因为CHIP项目负责人了解中国官方住户调查的一些缺陷,因此在CHIP项目调查中进行了一些改进。基于CHIP项目调查的代表性出版物包括里斯金、赵和李2000年,汗和里斯金2001年,以及里斯金2006年。与CHIP项目类似的研究路线来自王三桂(Sangui Wang)(和阿尔伯特·帕克(Albert Park))的工作,代表性出版物是帕克和王2001年。
上述半独立研究路线与官方文献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中国农村贫困自1978年以来究竟减少了多少。在CHIP项目学者和王的研究中,指出了官方农村贫困估算的某些方法论缺陷,并有限度地尝试提出了替代性估算(汗 1996)。他们批评的主要观点是,官方声称的1978年后农村贫困显著减少的说法被过分夸大了。他们坚持认为,1978年后中国农村减贫的实际表现不那么显著。然而,在指出这一点之后,并且没有为官方统计数据提供相应的替代方案,CHIP项目及相关研究转而得出结论,尽管官方统计数据存在各种问题,但1978年后中国农村减贫的记录仍然令人印象深刻,即使不如中国政府声称的那样显著。
CHIP项目在量化重估中国农村贫困方面的工作为沿着类似路线的进一步研究打开了大门。本博士论文旨在借鉴CHIP项目在官方统计数据问题上的发现,努力发扬CHIP项目的精神,提出一套1978年后中国农村贫困的替代性估算。
当前关于1978年后中国农村贫困状况的定性文献,主要采用案例研究方法,来源于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和社会工作等多个学科。这部分文献主要由不同学科背景的中国学者撰写,他们共同关注所谓的“三农问题(sannong wenti)”。这个术语最早由一位名叫李昌平(Changping Li)的经济学家在本世纪初提出,他当时担任中国中部湖北省(Hubei Province)一个乡镇的党委书记。他目睹了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的多方面经济危机,并于2000年初致信时任中国总理朱镕基(Zhu Rongji)报告了这场危机。这封信后来被收录进一本于2002年出版的书中。在信中,他将中国农民的生活描述为辛劳,中国农村贫困,中国农业危险(李昌平 2002)。由于农民、农村和农业这三个词在中文里共享一个共同的字(在英文中意为“agrarian”),他所描述的这些与涵盖“农民”、“农村”和“农业”的全面危机相关的问题开始被称为“三农问题”(以下简称TDAI)。他公开向中国总理报告(后来在中国广泛宣传)的这些问题是如此严重和令人震惊,以至于中国城市的普通公众和进步知识分子开始密切关注1978年后中国的农村危机。
2000年由上海社会学家曹锦清(Jinqing Cao)撰写的日记集《黄河边的中国》。些日记写于20世纪90年代曹锦清在中国农村沿黄河(Yellow River)岸,特别是河南省(Henan Province)进行田野调查期间。他记录并分析了与李昌平2002年发现的类似的农村问题。
陈桂棣(Chen)和吴春桃(Wu)2004年的著作将全国对农村危机的呐喊推向了又一个高潮。这两位作者花了三年时间调查安徽省(Anhui Province)农村,并报道了令人震惊的问题,其中一些问题政治敏感度如此之高,以至于这本书很快被政府查禁。
温铁军(Wen Tiejun)2005年和贺雪峰(He Xuefeng)2003年的著作引领了关于1978年后中国三农问题的两大有影响力的思潮。前者,温铁军,被广泛认为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晏阳初(James Yen)乡村建设运动(Rural Reconstruction Movement)的当代继承者,他认为中国农村必须通过自愿的农村合作社来拯救。他的提议基本上是改良主义的,因为他支持的农村合作社并非毛泽东时代的集体农村经济那种类型,而且他也不反对现存的、更广泛的市场资本主义环境。贺雪峰2003年的研究提出了解决当代中国农村危机(表现为三农问题)的社会文化方案。作者贺雪峰提出,中国农村必须建立在借鉴中国传统价值体系(如儒家思想)有益元素的社群自治基础上。
这批关于1978年后中国三农问题的定性文献中的所有著作都具有两个共同特征。首先,它们都指出了中国农村经济中对农村贫困具有重大影响的一个或多个负面方面。诸如耕地撂荒、水利基础设施失修、苛捐杂费与腐败、农村教育和医疗体系崩溃、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普遍存在,以及大量农村劳动力盲目涌向中国城市等问题,都对普通农村居民的生计造成了不利影响。其次,无论是由于该文献中的学者所持的改良主义进步(而非激进社会主义)视角,还是因为政府对中国学术界和媒体的控制,所有公开发表的关于三农问题的学者著作都只关注三农问题的某个特定方面,而没有探究其内在的相互联系,也没有追溯1978年后以三农问题形式表现出来的农村危机的深层原因。因此,这批文献往往是描述性的而非分析性的,并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问题导向的。它没有明确讨论去集体化或中国经济改革的其他组成部分在塑造三农问题或中国农村贫困状况方面的作用。
总而言之,关于1978年后中国农村贫困减少程度的定量文献中存在一些争议。由中国政府或世界银行提供的官方统计数据声称,农村贫困的减少记录是显著的。而像CHIP项目这样的半独立研究对官方说法的准确性提出了一些严重质疑,并认为1978年后的农村减贫是显著的,但不如官方统计数据声称的那样显著。关于中国农村多方面危机的定性文献揭示了1978年后农村贫困的严峻状况,但它缺乏一个可衡量的贫困概念,也没有试图考察1978年后中国农村普通居民生活条件恶化的深层原因。本博士论文旨在基于对1978年后中国农村贫困官方认知持批判态度的定量和定性文献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它将提出对1978年后中国农村贫困的替代性估算,并探讨当前状况的深层原因。
1.1.2 去集体化研究文献
现有文献中关于去集体化的研究比比皆是。尽管没有专门明确考察去集体化对中国农村贫困影响的研究,但许多著作确实考察了去集体化对中国农村经济的后果,这些后果与农村贫困状况相关。毫不奇怪,由于去集体化是从毛泽东时代集体经济到以家庭为基础的小农经济的农村经济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大多数关于去集体化的研究都或明或暗地涉及对1978年前后中国实行的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农村经济体制的一个或多个方面的比较。
广义而言,这些研究可以分为三类文献,分别侧重于去集体化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其不利后果,以及超越去集体化的因素。
1.1.2.1 去集体化的益处
关注去集体化经济效益的最突出研究涉及中国农民的劳动激励问题。这些研究共同的结论是,毛泽东时代集体经济(Maoist collective economy,此后简称MCE)因农民缺乏足够的劳动积极性而失败,而去集体化通过用一种基于个体农户的生产制度,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System,简称HRS)取代了MCE,从而拯救了中国农村经济。这一结论支持了中国政府关于MCE和HRS之间关键区别的官方学说,并已成为一种主流观点。
彼得·诺兰(Peter Nolan)(诺兰 1988)在这一领域做出了最具雄心的理论工作,他使用“管理上的规模不经济”(诺兰 1988:39-44)这一术语来表达以下观点:MCE中农民缺乏劳动激励的程度如此严重,以至于足以抵消甚至超过了集体农业本可以带来的技术性规模经济的潜在收益。该文献中的其他大部分著作倾向于依赖对某个村庄的案例研究,试图证明MCE在激励农民方面存在固有的失败。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包括弗里德曼(Friedman)等人 1991,李(Li)2005,倪(Nee)1985,安戈(Unger)1985,傅高义(Vogel)1989,沃森(Watson)1983,以及张乐天(Zhang Letian)1998。在下一章中,将对这些著作进行详细评述。
这些理论和实证研究共同认定的关于MCE未能为中国农民提供足够劳动激励的标准推理逻辑如下。在MCE中,当产出是集体劳动过程的产物时,不可能将报酬与工作挂钩,或将支付与劳动贡献联系起来。这是因为在最终的农产品中,无法区分一个农民的劳动贡献份额与另一个农民的劳动贡献份额。农业生产过程的漫长周期,例如从播种到收获的时间,进一步模糊了农民对于自身劳动与其在最终集体产品中所占份额之间联系的认知。因此,集体框架下的报酬方案往往趋于平均主义,从而无法为那些勤劳能干的农民提供足够的激励来维持其高水平的工作努力。普遍存在的搭便车现象成为典型结果。“按需分配”原则被纳入集体产品分配,进一步削弱了贡献与报酬之间的联系,使激励问题更加严重。此外,农业中的劳动监督比工业中更困难且成本更高,使得搭便车在集体农业中成为一种无法治愈且具有传染性的现象。因此,只有解散集体,恢复以个体农户为基本生产和核算单位,才能充分激励农民耕作。
另一类与MCE激励失败论点相关的研究采取了数学建模的形式,并侧重于激励问题的某个特定方面,即退出权。林毅夫(Justin Yifu Lin)认为,1959年后毛泽东时代集体缺乏退出权导致了普遍的怠工行为,也就是说,如果允许农民退出毛泽东时代的集体而不是强迫他们留在集体内,那么搭便车问题和由此产生的激励失败本可以避免(林 1990)。林毅夫的研究引发了激烈的讨论(董(Dong)和道(Dow)1993;麦克劳德(MacLeod)1993;刘(Liu)1993;孔(Kung)1993),林毅夫也对一些批评做出了回应(林 1993)。然而,所有这些研究都存在过度简化的形式建模问题,它们严重依赖简单的博弈论数学模型。总的来说,这场围绕林毅夫退出权假说展开的关于毛泽东时代集体农业激励问题的辩论具有严重的局限性。正如普特曼(Putterman)和斯基尔曼(Skillman)总结的那样,林毅夫及其批评者的解释都有待结合MCE丰富的历史细节进一步发展(普特曼和斯基尔曼 1993)。
除了去集体化在产生劳动激励方面据称的作用外,现有文献中的一些实证研究侧重于去集体化在提高农民收入或促进农业产出增长等领域在全国或地方层面产生的有益结果。波特夫妇(Potter and Potter)记录了广东省一个乡镇在1979年至1984年间年均人均收入增长24.5%,远高于10%至15%的年通货膨胀率(波特夫妇 1990)。就整个中国而言,1978年至1987年间,农村人均实际收入增长了约190%(倪和苏(Su)1990)。¹
关于农村收入增长的来源也存在讨论。根据尼古拉斯·拉迪(Nicolas Lardy)的观点,去集体化促进了基于比较优势的专业化和贸易,这产生了“纯粹的配置效率增益”,从而导致了农业收入的增长(拉迪 1985)。其他研究提到了非农就业对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性(黄(Huang)1989,维克(Veeck)和潘乃尔(Pannell)1989,黄 1990)。
林毅夫提供了一项讨论去集体化在促进农业产出增长方面作用的特别有影响力的研究。他的研究是一项计量经济学研究,试图解释1978-1987年间中国农村农业产出增长的来源。他的结论是,在1978-1984年间,导致这种增长的最大因素是去集体化(林 1992)。
然而,林毅夫的计量经济学研究至少包含以下关键缺陷。
林毅夫研究的第一个关键缺陷是计量经济学模型的设置过于简单化。可能对1978年后产出增长做出贡献的潜在重要因素包括水利和土地改良项目等生产性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和使用情况、更高水平的农药和改良种子应用,以及更有利的气候条件。然而,这些潜在的重要因素都被排除在数学函数之外。仅有有限的一部分此类因素被纳入林毅夫计量经济模型的设置中:土地规模、拖拉机和役畜,以及化肥。
其次,在比较1978-1984年和1984-1987年的产出增长时,林毅夫含蓄地得出结论,去集体化是一次性地刺激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在去集体化完成之后,影响产出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将变成贸易条件,即农产品价格相对于制成品投入价格。这一结论实际上极大地限制了通过解决劳动激励问题而带来的去集体化的所谓益处,因为这些益处仅在去集体化完成之前和完成之时才存在。一旦去集体化完成,进一步获益的空间将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1984年之后所有年份里管制较少的市场不稳定性所带来的影响。
因此,那种认为林毅夫1992年的研究是一项明确证明去集体化为中国农民提供了足够劳动激励并且是后续农业增长最主要因素的普遍看法,应当进行仔细的重新评估。
1.1.2.2 去集体化的代价
值得注意的是,强调去集体化对中国农村经济益处的研究在现有文献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强调去集体化对中国农村经济不利影响的著作则被边缘化。尽管处于非主流地位,但后一类著作确实揭示了去集体化可能给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带来巨大代价的某些方面。
该文献强调的最突出问题是从MCE向HRS过渡过程中规模经济的显著损失。由于团队耕作的解散和土地分割成小块供家庭耕作,规模经济在许多不同方面都遭受了损失,并且这些损失相互交织。农田碎片化导致播种面积减少,因为部分土地不得不用于不同农户地块之间的分隔。更重要的是,碎片化的土地使得机械化更难实施,并严重破坏了许多生产性基础设施(特别是灌溉和排水设施),这些设施只有在土地大面积整合时才能处于最佳状态。个体农户耕作的实践进一步造成了一种局面,即不同农户之间的协调变得更加困难,而他们之间的纠纷则更加频繁。结果是多方面的:由于单个农户进行新技术试验的风险更大,试验进展缓慢;现有集体基础设施的定期维护和新基础设施的建设脱轨;出现了各种负外部性案例,特别是在使用对环境和土壤质量有害的现代工业投入品方面等等(韩丁(Hinton)1990,戴尔·温 2005,崔格(Zweig)1985,波特夫妇 1990)。
规模经济损失问题也与劳动激励问题密切相关。主流文献侧重于毛泽东时代劳动激励失败的论点,很大程度上选择忽略规模经济损失的问题,因为在他们看来,如果缺乏劳动激励,这些规模经济仅仅是潜在的,无法实现。因此,毛泽东时代的集体是否确实受到固有的激励农民劳动失败的困扰,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但在去集体化运动之前,主流观点实际上是相反的:毛泽东时代的集体在激励农民劳动方面表现非常好。这一点在派往中国的国际组织代表团的官方报告(联合国粮农组织(FAO)1978)和独立学者进行的理论分析(里斯金 1975)中都得到了明确体现。即使在去集体化完成之后,仍然存在一些理论观点认为激励失败并非毛泽东时代集体的固有特征。例如,路易斯·普特曼(Louis Putterman)得出结论,毛泽东时代的集体并非内在地导致平均主义的分配方案,这更多的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要求(普特曼 1985)。
也许在劳动激励问题上,支持毛泽东时代集体的更有力的论据来自实证研究。韩丁、高默波(Mobo Gao)和韩东屏(Dongping Han)考察了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三个不同中国村庄的变化,发现劳动激励并非MCE的固有问题。相反,他们生动地描述了团队耕作和集体管理如何通过普遍的试错过程,特别是通过赋予普通农民政治权力而逐步改进(韩丁 1983,高 2007,韩 2008)。此外,韩丁利用20世纪50年代初至中期的中国渐进式集体化进程的经验表明,不应将MCE理解为一个外部掠夺性国家强加给坚持维护其原有家庭耕作方式的中国地方农民社群的制度(韩丁 1994)。
另一个与中国农村劳动激励相关的问题是中国农民对去集体化运动的态度。主流文献大多将去集体化描述为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基层农民主动发起,政府仅仅回应农民的地方呼吁。然而,这种刻板印象遭到了记录农民和干部抵制中央政府的文献的有力批评。去集体化在实际操作中是一场由中央领导层中有权势的官员精心协调并指导下级领导层和基层的运动。它以“一刀切”的方式实施,即强加于全中国。农村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尤其抵制这场运动,但在来自上层的政治压力面前大多失败了(Zweig 1983,萧凤霞(Siu)1989,韩丁 1990,钟Chung,2000)。
1.1.2.3 超越去集体化
在前述两类文献——一类强调去集体化对中国农村经济的益处,另一类强调其代价——之间,存在第三类文献,侧重于从毛泽东时代延续到后去集体化时代的促进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积极力量。这些力量主要涉及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发展,特别是MCE所培育的发展,它们为MCE被HRS取代后的进一步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来自克里斯·布拉莫尔(Chris Bramall)。他坚持认为应采用“学习曲线”的方法来看待1978年前后中国经济发生的变化。他特别呼吁注意这样一个事实:不应仅仅因为后去集体化时代的经济成就发生在去集体化之后,就将其视为纯粹是去集体化运动的结果。必须关注那些在MCE中得到培育,并在MCE解体后继续发挥作用或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力量。他分析的重点最初是农村工业化,后来扩展到更广泛的问题(布拉莫尔 2007, 2009)。
黄宗智(Philip Huang)的研究也是一个有趣的案例。他的分析侧重于真正有意义的发展是否可能发生。他使用“有增长无发展”和“内卷化”这两个词来描述这样一种情况:劳动边际生产率在下降,而为了增加总产出,劳动投入仍在不断增加。
公平地说,由于这种对长期技术发展的关注,即跨越去集体化前后的两个时代,黄宗智对对比毛泽东时代与1978年后时代不感兴趣。从这个角度来看,黄宗智的研究可以用来证明毛泽东时代为毛泽东时代和1978年后时代的真正有意义的发展奠定了一些有利条件。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黄宗智的研究也可以用来支持去集体化促进了真正发展的论点,因为黄宗智记录了去集体化发生后,由于农业活动多样化和非农就业,农民家庭收入的增长。值得注意的是,黄宗智本人并未明确讨论去集体化在中国农村经济真正发展方面的作用。
总之,关于去集体化对中国农村经济影响的现有文献的三种类型,对于本博士论文研究的目的都是有用的。它们指出了去集体化可能影响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贫困状况的三种不同方式:产生新的积极力量以促进发展和减少贫困,产生新的消极力量以阻碍发展和加剧贫困,以及继承毛泽东时代准备好的现有力量。
1.2 理解去集体化的影响
第二章的核心任务是分析去集体化对农村贫困的影响。这项任务涉及两个步骤:1)理解去集体化在中国农村产生的根本性制度变迁;2)分析去集体化影响农村贫困的渠道。
1.2.1 双重制度分析法
在考察去集体化的内涵时,采用了一种双重制度分析法。说它是制度性的,是因为去集体化被理解为一个产生了深刻制度变迁的过程——它终结了中国农村的一种旧经济制度——MCE,并引入了一种新制度——HRS。因此,理解去集体化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应从分析HRS与MCE的关系入手。
这种对去集体化的制度分析法抓住了HRS与MCE相关的两种方式。首先,它分析了HRS相对于MCE在对中国农村经济的影响及其对中国农村贫困的启示方面的优缺点。其次,它分析了HRS可能如何与MCE的遗产互动,即继承MCE在毛泽东时代培育并传承到1978年后时代的积极和/或消极力量。因此,这种双重制度分析法包含了关于去集体化如何影响中国农村贫困的两个分析要素,一个比较要素(比较HRS与MCE)和一个互动要素(分析去集体化后几年MCE的残余力量)。互动要素的目的是将去集体化对中国农村贫困的独特影响与MCE在去集体化前时代产生的影响区分开来。
1.2.2 影响渠道
去集体化通过一系列因果渠道影响中国农村贫困。首先,去集体化对中国农村经济活动的三个领域产生影响:生产、交换和分配;其次,这些对三个领域的影响进而影响农村居民的收入以及贫困线所需的必要开支;第三,这些收入和必要开支的变化随后决定了农村贫困的状况。²
第一组因果渠道,即去集体化对生产、交换和分配领域的影响,是第二章的分析重点。如上所述,这些影响将通过分析HRS应如何与MCE进行比较以及如何与MCE互动来加以证明。
1.3 估算农村减贫状况
第三章承担了两项主要的分析任务。第一项任务是批判性地审查官方的农村减贫统计数据,并对1978年后中国农村的减贫绩效提供一个替代性估算。第二项任务是分析去集体化对这一估算绩效所做的贡献。
由于本博士论文中使用的贫困概念服务于分析去集体化影响的目的,因此它与当前文献中某些使用方式有所不同。因此,下文将做一些重要说明,以阐明本博士论文如何看待和评估贫困。
首先,关于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本博士论文使用的贫困概念是绝对贫困,而非相对贫困。
其次,关于衡量贫困所使用的指数,仅使用贫困发生率来衡量贫困;其他指数如贫困差距和平方贫困差距则不使用。
第三,关于是检查收入还是支出来对照贫困线以确定农村居民是否贫困,本博士论文选择收入(即基于收入的贫困衡量,而非基于支出的衡量)。
第四,关于贫困趋势(一个“流量”概念)与贫困状况(一个“存量”概念),重点放在贫困趋势上,即贫困减少了多少,而不是贫困状况,即仍有多少贫困存在。后者取决于对合适的“贫困线”的不同定义。就目前的目的而言,重要的不是对贫困水平的替代性衡量,而是农村贫困——无论贫困线如何定义——自去集体化以来是如何变化的。由于数据可得性有限,在本博士论文中,作者仅能提供对2007年贫困水平的估算,这一估算在1984年和1978年官方估算的支持下³,使得本博士论文能够聚焦于1978-2007年这一时间段及其子时段1984-2007年和1978-1984年的贫困趋势。
第五,关于收入贫困与非收入贫困,本博士论文采用收入贫困的概念,并认为非收入贫困应被整合到收入贫困中,特别是在1978年后中国农村的背景下。
1.3.1 绝对贫困
本博士论文采用绝对贫困的方法。贫困可以相对或绝对地定义。相对贫困通常基于一条可变的贫困线,该贫困线与一个社会的人均收入挂钩,因此随其整体经济繁荣水平的变化而变化。因此,相对贫困的概念与不平等的概念有所重叠。
然而,在本博士论文中,贫困概念是以绝对方式使用的,即基于一条恒定的贫困线,该贫困线由满足日常生活的最低物质消费需求所决定的,而不论社会整体经济繁荣程度如何.4以绝对方式定义,即使在不平等恶化的情况下,贫困状况也可能改善5。在中国不平等状况众所周知地恶化的时代,考察穷人的绝对经济地位是改善了还是下降了,变得至关重要。
1.3.2 贫困发生率
本博士论文使用贫困发生率来衡量贫困。贫困发生率定义为福利水平低于贫困线的人口比例。在流行的福斯特-格里尔-索贝克(Foster-Greer-Thorbecke,FGT)贫困衡量指标体系中的三个重要指标中,贫困发生率是使用最广泛且直观上最清晰的一个。尽管另外两个指标,即贫困差距指数和平方贫困差距指数,也提供了关于贫困人口贫困程度的有用信息,但出于篇幅和简明性的考虑,本博士论文将仅考察贫困发生率。⁶
1.3.3 基于收入的衡量
本博士论文采用基于收入的贫困衡量方法。在估算出贫困线之后,有两种方法可以确定某个个体或家庭是否处于贫困状态。基于收入的贫困衡量方法是将收入水平与贫困线进行比较。7如果个体的收入或家庭的人均收入低于贫困线,则所研究的个人(们)被视为处于贫困状态。相反,基于支出的方法则考察个体或家庭的支出水平,并将其与贫困线进行比较以确定贫困状况。两种方法各有优缺点。本博士论文仅采用基于收入的衡量方法,原因是数据可得性和简明性。
1.3.4 贫困趋势
本博士论文更侧重于经济改革时期中国农村贫困的总体趋势,即去集体化后农村贫困减少的总绩效,而较少关注任何特定时间的农村贫困状况,即在某一年仍有多少贫困人口。要充分探讨估算某一年中国农村贫困的问题,就必须确定一个被认为是适当贫困线的物质生活水平。其中一项核心任务包括评估所有当前使用的贫困线的相对优缺点。这本身就是一个重要课题,但考虑到本博士论文的篇幅及其目的(考察去集体化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在本博士论文中,我将采用一条特定的贫困线(最初的官方贫困线),并评估去集体化后农村贫困总量减少了多少(即农村贫困趋势),同时随时间推移遵循同一条贫困线(实际意义上,而非名义意义上)。⁸
1.3.5 收入贫困
本博士论文将非收入贫困的概念整合到收入贫困的概念中。⁹非收入贫困的概念,正如其在当前文献中的使用,具有模糊的理论基础。从理论上讲,这个概念只有在人们无论拥有多少收入都无法获得满足基本消费需求的某些必需品和服务的情况下才有意义。
然而,在当前文献中,非收入贫困的概念主要用于两种方式,而这两种方式都与这种合理的含义关系不大。在非收入贫困的第一种用法中,学者们认为人们无权获得某些对他们的贫困状况有重大影响的资源和机会,如教育、健康和就业。这种第一种思维方式混淆了贫困的原因与贫困本身(福斯特(Förster)等人 2004,以及阿里夫(Arif)2006)。贫困的原因无疑是一个与贫困相关的重要课题(本博士论文正是对此课题的研究),但它在分析上也与贫困本身的衡量截然不同。在非收入贫困的第二种用法中,学者们将收入仅仅视为人们福祉的一个可能维度,并将教育、健康、住房等其他事物也视为与衡量贫困相关的福祉组合的重要维度(萨恩(Sahn)1999,以及博阿里尼(Boarini)和德尔科勒(d’Ercole)2008)。这种第二种思维方式将收入和其他项目视为贫困的平行维度。本博士论文采取的立场是,收入不应与其他那些贫困的“维度”并列,因为它根本就是其他“维度”应被转换成的公分母。
还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某些商品和服务无论人们收入水平如何都无法获得的情况下,这些商品和服务通常也可以通过查询其在具有相似条件的地区或替代商品和服务的成本的通行价格来转换为收入。¹⁰此外,当前文献中使用非收入贫困概念来理解教育和健康等商品和服务可获得性的学者,往往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大多数情况下,穷人仅仅因为收入不足而被剥夺了获得这些商品和服务的机会(例如,参见博阿里尼和德尔科勒 2008,第178页)。
在本博士论文的背景下,将非收入贫困的概念整合到收入贫困的概念中就显得更为必要。这是因为去集体化迫使农村居民为诸如健康和教育等基本商品和服务自掏腰包,而在去集体化之前,这些费用主要由集体和国家预算承担。通过将这些商品和服务保留在收入贫困的概念之内并估算其收入等值,MCE时代与HRS时代农村贫困的对比,以及因此去集体化对中国农村贫困的影响,将比分别处理非收入贫困和收入贫困的情况更为清晰。
第二章 去集体化对农村贫困的后果
2.1 去集体化的性质
作为一个发生在1978-1984年间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HRS)取代毛泽东时代集体经济(MCE)的历史进程,去集体化深刻地改变了管辖中国农村的经济制度。尽管它发生的背景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不同,但去集体化的一揽子方案在性质上与新自由主义相似。¹¹借用常用于描述新自由主义特征的术语,去集体化方案的三个组成部分可分别称为事实上的私有化、管理放松管制和市场自由化。
2.1.1 事实上的私有化
去集体化方案的第一个组成部分,即事实上的私有化,包括两个要素,分别涉及农业和非农业部门。
第一个要素是将过去集体耕种的土地分割成小块,承包给个体农户。土地所有权在法律上仍然是集体的,但从农场获取收益的基本权利则归于各个家庭。这一变化的核心在于,每个个体农户都要对其家庭农场的经营盈亏负责,特别是在生产成本和销售收入等关键财务方面。
第二个要素是将集体所有的非农企业承包给个体家庭。同样,这些企业在法律上仍归村集体所有,但现在由根据市场资本主义的竞争和利润最大化逻辑获得承包权的家庭经营。
尽管这两个要素分别针对农业和非农业部门,但它们具有相同的制度特征:生产资料(土地或企业)仅在法律意义上为集体所有;在实际的、有效的意义上则为私人所有。因此称之为事实上的私有化。两者之间唯一的关键区别在于,在非农业部门,经营企业的家庭通常雇佣其他农村居民工作,即代表一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在农业部门,正常状态是自营职业,即代表一种小资产阶级生产方式。
2.1.2 管理放松管制
去集体化方案的第二个组成部分,即管理放松管制,与第一个组成部分事实上的私有化高度相关,因为以独家责任经营家庭农场必然导致,过去在毛泽东时代集体中占主导地位的队组式农业管理的瓦解或放松管制。
现在,通常情况下,个体农户自愿做出关键的经营决策,例如种什么、何时种、如何种等等,并对他们决策的结果负责,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他们不再需要听从某些集体管理的决策,因为作为生产实体的生产队以及大队和公社已经消失了。某些公共产品方面,例如集体生产性基础设施,成为一个灰色地带,村干部现在作为与经济活动分离的农民社区的公共领导人,已无法再通过直接的行政手段组织农民从事生产活动。
然而,对农户生产决策的放松管制绝非绝对。中国政府仍然保留对某些战略产品(如粮食和棉花)生产进行管制的权力,特别是以对特定地理区域施加配额的形式。
2.1.3 市场自由化
去集体化方案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是农村市场的自由化。这主要涉及农产品与非农产品(作为农业投入品或农村消费品)之间的贸易条件。¹²
原则上,中国政府给予市场为农产品定价的自由。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农产品的价格并非完全由市场决定,特别是当政府认为有必要实行配额时。对于强制性配额内的产品有政府收购价格,通常对于超配额产品也会有更有利的政府价格。然而,总的趋势是政府逐步放宽这些干预措施,除非在紧急情况下。
值得注意的是,市场自由化不仅仅是农产品的自由化,也包括非农产品的自由化。这对农村贸易条件产生了严重影响。如果任由市场力量决定通行价格,那么大量的小农户在面对少数遵循市场资本主义利润最大化原则并可能拥有寡头垄断权力的非农产品和服务生产者时,通常会显得无能为力。
去集体化在中国农村带来的这三个制度变迁的组成部分,对农村贫困人口的经济状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章接下来的三个部分将分别在考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HRS)与毛泽东时代集体经济(MCE)相比较以及相互作用的框架下,分析其对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后果。
2.2 生产领域
在本节中,分析的重点是去集体化对中国农村以家庭为基础的(或小农的,或小资产阶级的)农业生产的后果。其对农村居民参与以企业为基础的生产的影响将在下文2.3节中讨论,该节的重点是分配领域。
关于去集体化对中国小农农业生产影响的讨论分三步进行。前两步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HRS)同毛泽东时代集体经济(MCE)的比较有关,即HRS在塑造中国农村农业生产条件方面与MCE有何不同表现。由于HRS与MCE相比既有优点也有缺点,因此分别用两个不同的步骤来讨论它们。
第一步将讨论HRS与MCE相比的缺点,或者说HRS对中国农业生产造成的不利影响。
第二步将讨论HRS相对于MCE的优势,或其对中国农业生产的有利影响。
第三步将讨论HRS与MCE之间的相互作用,或HRS如何继承了MCE产生的力量。
2.2.1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毛泽东时代集体经济的比较
本小节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HRS)和毛泽东时代集体经济(MCE)的比较分两步进行。
第一步,在与MCE比较的背景下,讨论去集体化可能如何阻碍了中国农村经济发展。重点尤其放在从MCE向HRS过渡可能导致的规模经济损失上。第二步,讨论的重点将转向去集体化相对于MCE可能如何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在劳动激励问题上。
2.2.1.1 规模经济
毛泽东时代集体经济(MCE)的制度体现在人民公社中,在一个相当于整个乡镇的区域内,农村居民被组织成一个三级所有的集体所有制、集体生产和集体分配结构,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¹³由于在远大于个体农户规模的各种农业(以及非农业)部门的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被集中起来,因此有可能实现显著的规模经济。
因此,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HRS)取代毛泽东时代集体经济(MCE)可能导致农业部门规模经济的重大损失。主流文献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这种可能性,因为他们认为,由于激励机制的失败,MCE从一开始就未能实现任何有意义的规模经济,因此也就谈不上后来被HRS浪费掉。
理论上,在MCE的农业部门,潜在的规模经济可能出现在两种主要情景中。
在第一种情景中,通过将某一特定类型的生产性投入(劳动力、土地或其他生产资料)集中起来,即增加这种投入的数量,可能会实现一种“1+1>2”的聚合效应。例如,与其他同事一起工作可能会让人感受到相互支持或相互竞争的氛围,从而可能产生更高水平的工作努力和劳动生产率。另一个例子是,当土地集中起来耕种时,就不需要在属于不同农户的地块之间保留分隔物或田埂。因此,有更多的土地可用于耕种。再一个例子是,可以启动更深层次的劳动分工,不同的人专门从事不同的技能,从而加快生产速度并提高产量。
在第二种情景中,增加某种生产性投入的数量以促进另一种生产性投入的运作。例如,当土地从个体农户手中集中起来时,拖拉机的使用变得可行或经济。另一个例子是将农业剩余劳动力(特别是在冬季或农闲季节)转化为大规模的生产性基础设施项目,即将劳动力转化为“资本”。再一个例子是关于试验或应用新的农业技术或方法。这在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业中通常很困难,因为一次失败通常会威胁到整个家庭的生计。但在MCE下,当土地集中起来时,通过只将一小部分农田用于试验或应用新技术或方法来鼓励创新,因为失败的风险可以由整个集体分担。
对照这两种理论情景,仔细审视非主流文献和经验材料后发现,在从MCE向HRS过渡之后,中国农业确实损失了显著的规模经济。
对照第一个理论情景,最显著的现象之一是土地的浪费。随着去集体化,大片集体经营的农田被分割成每户多块的小块土地,分散在村庄各处,对应着不同的位置和土壤肥力水平。韩丁生动地将这些小块农田称为“面条地”。超过5%的土地因小块土地之间的边界和田埂而损失(波特夫妇 1990,第175-6页;韩丁 1990,第14-5,64-6页)。
一个相关的土地浪费现象是,一些农户发现种地无利可图而抛荒。李昌平在其致朱总理的信中,报告了他在担任党委书记的华中某乡镇三农问题的悲惨状况。信中强调的一个惊人事实是农民大规模抛荒(总耕地的65%被抛荒)并迁往中国城市(超过83%的农村劳动力迁出)。而且这并非是高高兴兴地抛荒离乡去高薪的城市部门赚大钱。信中描写的留守家人送别迁徙亲人的场面对未来的景象令人震惊和沮丧。这更像是难民逃离灾区,对未来没有任何希望(李昌平 2002,第20-7页)14。类似的情况在现有文献的其他著作中也有记载(萧凤霞 1989,第276页;黄 1990,第245页;傅高义 1989,第168页;韩丁 1990,第78页)。这里必须澄清的是,本段描述的土地抛荒类型是去集体化的间接结果,因为去集体化直接导致了诸如农业贸易条件恶化等因素(详见2.3.1节),而这些因素反过来又造成了土地抛荒。
从MCE向HRS的过渡也造成了本可以通过保留MCE下发展起来的那种更深层次的劳动分工而获得的规模经济的损失。在MCE下农业机械化和农村工业化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地区,去集体化后许多农民被迫在农业生产中以劳动力替代机器,从而对其从事利润更高的非农活动的时间分配产生了不利影响。这是去集体化在相对发达的农村地区遭遇广泛抵制的一个重要原因(萧凤霞 1989,第280-1页;崔格 1985,第161页)。
另一个与HRS因劳动分工水平较低而导致的规模经济损失相关的重要证据,来自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农民近期的反应。在三农问题危机不断深化的背景下,近年来中国农村出现了一场新的运动。这场运动旨在通过农民自发组织成新的合作社,以期利用HRS无法提供的某些规模经济。河北省(Hebei Province)青龙县(Qinglong County)的大森店水果合作社就是一个例子。截至2007年夏天,青龙县山区大森店村(Dasendian Village)已有52户农户加入该合作社。他们已经能够组建一个由合作社成员中最有技术的23名农民组成的维修队。他们共同承担了合作社所有成员拥有的所有果树的日常维护工作。结果,日常维护成本一直保持在非常低的水平——每年每棵树2元(该合作社成员因此集体节省了1000个工日或每年3万元),此外,由于这支常备队伍的专业技能,维护质量也得到了明显改善(大森店果品专业合作社 2008,第3-4页)。15
按照上文概述的第二种理论情景,也出现了显著的规模经济损失。
土地碎片化和分散经营使得拖拉机和其他类型的现代农业机械难以用于农业生产活动。韩丁记录道,在山西省长弓村(Long Bow Village),去集体化将整合的土地分割成小块后,各种机械都生锈闲置了(韩丁 1990,第15页)。在黑龙江省绥化地区(Suihua Prefecture),1983年去集体化之前曾有5058台大型拖拉机。然而,去集体化之后,到1989年底,这一数字下降到3767台。结果,自去集体化以来,许多土地已有六七年未曾耕犁,导致抗旱防洪能力下降(梅(Mei)1999,第18-19页)。在某些地区,由于土地过度碎片化,甚至连役畜的使用也变得不经济,役畜数量迅速减少。例如,在四川省泸县(Lu County),1980年去集体化之前曾有4.95万头耕牛。去集体化之后,耕牛数量在1984年下降到4.06万头,并在1986年进一步下降到3.36万头。(梅 1999,第14页)。
也许最令人担忧的是,集体生产性基础设施项目遭到了严重破坏:现有的无法得到良好维护,新的也很少启动。农民自身在基本建设,主要是农业基础设施方面的劳动投入,从20世纪70年代末高达每年80亿个工作日下降到80年代末不足其四分之一(韩丁 1990,第145页)。在某些情况下,现有的大型水利工程不仅无人照管,而且由于不同地方在用水问题上的冲突而被人为破坏。例如,毛泽东时代中国最著名和最成功的灌溉工程——河南省林县(Lin County)的红旗渠,在1987年7月的一个干旱季节,由于缺乏维护和上游农民的蓄意破坏,无法为邻近的农田和农民社区提供足够的水。这不仅导致该县80万亩总耕地中的13万亩颗粒无收,还迫使9.7万当地农民远距离购水(梅 1998,第16页)。
1978年后中国农村集体生产性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恶化,即使在客观报道中国农村状况的现有主流文献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记录。一位关于中国三农问题的权威且广具影响力的专家陆学艺(Xueyi Lu),对20世纪80年代末期农村基础设施日益恶化的状况进行了令人震惊的描述:
农业的严峻形势体现在生产性基础设施的恶化……土壤肥力正在下降,有机质含量呈下降趋势。例如,在以黑土闻名的黑龙江省,有机质含量过去为7-8%……现在降至5-6%。在山海关(Shanhaiguan)以内的大部分地区,有机质含量仅为1-2%。1976年,施用有机肥的耕地面积为1.5亿亩。1987年,这一数字仅为6218万亩,减少了60%……有效灌溉面积逐年减少……自1980年以来从未修建过大型水库……1980年以前,每年新增灌溉农田800万至1000万亩。1980年以后,不仅灌溉面积没有增加,现有存量反而下降了。官方统计报告称,1986年有效灌溉面积比1980年减少了1000万亩。实际数字远大于此。目前中国约有3亿亩农田因缺乏灌溉而常年干旱……农业生产工具也已落后。由于旧机械老化,从1980年到1986年,全国机械化耕种面积减少了6800万亩,即11.1%。(陆学艺 1989,第5页)
其他报告也证实了这一令人担忧的景象。安徽省是最早开始去集体化的地区之一。1986年一份广为流传的报告将该地区水利系统的恶化描述为悲剧性的。截至1984年底,在安徽省淮北(Huaibei)地区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修建的13.8万口机井中,只有3.4万口仍能完全正常运行。1985年7月和8月,当该地区遭受干旱袭击时,只有大约4000口井能够有效地用于抗旱。造成这种大规模水利基础设施破坏的主要原因包括将公共沟渠转为私有土地、缺乏日常维护以及机井电泵被盗,所有这些都是由去集体化的力量驱动的(张传轩(Zhang Chuanxuan)和吴思(Wu Si)1986)。到21世纪中期,在中国所有农村地区,1978年前修建的8.4万座水库中,约有三分之一已经失修(杨兰举(Yang Lanju)等人 2005,第75页)。
从以下三个表格可以清楚地看出,从MCE到HRS的过渡在很大程度上使农村集体生产性基础设施项目脱轨,损害了中国农村的农业生产。

表2.1显示了毛泽东时代与后毛泽东时代在现存水库数量上的差异。尽管在毛泽东时代(由于1952年和1962年¹⁶的数据不可得,此处的毛泽东时代指1949-1978年期间),大型、中型和小型水库的数量都迅速增加,但在后毛泽东时代,这些数量却停滞不前。

表2.2显示了毛泽东时代与后毛泽东时代在有效灌溉面积上的巨大差异。无论毛泽东时代是指1962-1978年还是1952-1978年,毛泽东时代有效灌溉面积的年均增长率大约是后毛泽东时代的三到四倍。
从假设的角度讲,可以认为,如果我们在1978年后时期看到水库建设或有效灌溉面积增长率下降的趋势,这可能是因为中国耕地所需的大部分灌溉设施已在1978年前时期建成,因此之后建设新设施的需求不大。这一论点暗含了对建设额外设施的边际效益与所产生边际成本的比较。基于这种比较,该论点认为,自1978年以来中国农业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进展缓慢,是因为其边际成本已日益趋向于超过其边际效益。然而,从去集体化以来中国农业的经验来看,这一假设性论点具有误导性。
首先,由于其特殊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中国农业易受干旱和洪涝灾害的影响,自古以来就严重依赖健全的水利设施来确保可靠的收成(朱(Zhu)等人 1992,第384,442页)。理想情况下,即如果不考虑建设水利设施的成本,中国所有耕地的作物产量都可能受益于新建或维护良好的水利设施。现有文献中没有提及有效灌溉面积与需要灌溉的总耕地面积之比,这一事实似乎支持了这一判断。事实上,1978年后时期的政府报告一直关注在有效灌溉面积基本停滞在仍低于总耕地面积一半的水平的背景下,新增了多少令人欣喜的有效灌溉面积,或者不幸损失了多少现有有效灌溉面积。17即使考虑到成本方面,仍有证据表明需要建设新的水利设施并良好维护现有的设施,因为效益大于成本。18
其次,如果成本因素导致了1978年后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放缓,那么成本上升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去集体化本身。将经营自家生意的个体农户组织起来,共同行动建设公共基础设施,已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耗资巨大。曹志勇(Cao Zhiyong)2006年的评论具有代表性: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场改革对农业水利基础设施造成了明显的不利影响。更具体地说,这是因为土地被分割给了成千上万的个体农户,他们每个人都只关注自己的农田,而对包括农业水利基础设施在内的公共事业缺乏足够的关注和支持。”(曹志勇 2006,第49页)
从前述现有灌溉设施维护不善的事实,以及下文对表2.3的讨论来看,有理由认为1978年后时期缺乏灌溉建设的努力并非因为缺乏需求,而是因为去集体化和其他政治经济因素的不利影响。

表2.3显示,与毛泽东时代相比,后毛泽东时代自然灾害转化为实际灾害的比例更高。这似乎是一个令人惊讶的结果,因为尽管在后毛泽东时代,现有水库和有效灌溉面积的年均增长率显著放缓,但现有水库的总数和总有效灌溉面积仍然高于毛泽东时代。这背后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由于农村集体的解体,即使可以修建新的水库和灌溉新的土地,新旧水利工程都未能得到良好维护。根据最近的一篇新闻报道(郭芳(Guo Fang)等人 2011),中国现有水库中约有一半是病险水库——它们已经严重老化,坝体可能垮塌。在这方面,官方关于有效灌溉面积数据的可靠性应受到质疑——过时和破旧的灌溉设施不能说是真正有效的。
2.2.1.2 劳动激励
从毛泽东时代集体经济(MCE)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HRS)的转变也可能对农民的劳动激励产生重大影响。传统观点认为,去集体化解决了MCE固有的劳动激励失灵问题。有人认为,MCE下的农民缺乏劳动积极性,因为他们的劳动付出无法根据其对集体最终产品的个人贡献得到报酬(集体耕作使得无法确定集体劳动过程产物中个人的份额)。这是一个典型的搭便车论点。然而,这是否真的适用于MCE,比通常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仔细思考后,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讨论,或者说可以看作两个相互关联但又有所区别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MCE是否注定无法为农民提供足够的劳动积极性?第二个问题是:在MCE的实际运作中是否发现了激励问题,如果是,其严重程度如何?第一个问题更具理论性,质疑MCE在没有激励失灵的情况下运作的可能性,或者MCE遭受激励失灵的必然性。第二个问题更具经验性,考察在MCE下激励失灵的普遍程度,即使MCE并非必然注定激励失灵。
2.2.1.2.1 毛泽东时代集体经济的激励结构
首先,让我们考察第一个问题,即毛泽东时代集体经济(MCE)是否必然受到激励失灵的困扰。传统观点对此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其主要依据有两点,即缺乏有效的监督以及在MCE下无法区分集体产品中的个人份额。然而,当我们深入探究MCE的实际运作时,这两点似乎都存在问题。
其中一点是关于有效监督。如果MCE下确实缺乏有效监督,那么集体产品的分配就不得不趋于平均主义,因为没有办法判断对集体产品的相对贡献。但这并不一定会导致激励失灵。这里我们必须区分两种情况,这取决于农民的心态。如果农民倾向于故意搭便车,也就是说,蓄意占其他农民的便宜,那么知道不存在有效监督并且分配是平均主义的,就会导致他们怠工。但这仅仅是一个假设,它基于缺乏经验证据的新古典主义“经济人”(homo economicus)(或理性经济人)模型,尤其是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背景下(下文对毛泽东时代中国农民心态的阶级分析将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如果农民是潜在具有互惠思想的人,那么在不知道其他人怠工的情况下,他们不一定会怠工。¹⁹因此,即使像传统观点所说的那样,MCE下确实没有对劳动贡献进行有效监督,农民很可能也会选择完成分配给他们的工作而不怠工。如果大多数农民都具有互惠思想,那么很少有人会怠工,怠工也不会对集体农业生产产生重大影响。
但缺乏有效的劳动监督并非MCE所固有的。相反,MCE下的两种制度可能提供有效的劳动监督:队长监督和相互监督。队长按理负责分配任务和监督劳动。即使由于时间和精力有限,队长无法监督所有农民的劳动,队员们也可能相互监督各自的劳动。一种常用的衡量农民对集体产品劳动贡献的机制就是基于这种监督。在这种机制中,所有农民的工分都基于两个部分:反映个体农民体力和技能的基本分,以及反映个体农民劳动态度和劳动努力程度的努力分。所有这些工分都将由个人自报并集体评议。这种机制的集体评议要素是基于相互监督的,因为劳动过程是集体的。队长将主持讨论基本分和努力分的会议。队长的意见(大概反映了他或她对农民的监督)也会对这类会议的进程产生影响。
传统观点可以继续辩称,即使确实存在这样的队长监督和相互监督,仅仅因为在MCE下无法区分集体产品中的个人份额,这种监督也无法为农民产生量化的、精确的、客观的工分。也就是说,自报和集体评议的会议只会导致低效的争吵和平均主义的分配结果,从而挫伤每个人的劳动积极性。仔细审视后,这种论点被证明是有问题的。它曲解了队长监督和相互监督的作用,以及对量化的、精确的和客观的工分衡量的需求。
正因为集体耕作过程使得无法精确衡量个人在集体产品中的份额,农民们在确定工分的会议上就不会将此设定为目标。农民们明白,他们对彼此体力、技能和努力程度的了解并非精确、绝对和客观量化的。因此,对于他们相互估计彼此的工分而言,会存在一个可接受的值域,而不是一个单一的值。只要自报和集体评议的要素都落在这个值域内,农民们就会容忍彼此相互估计的差异。因此,农民们很可能在不挫伤其劳动积极性的情况下就工分分配达成一致。
必须澄清的是,上述讨论并不意味着在MCE下永远不会发生激励问题。相反,它们只是表明激励失灵并非MCE所固有的,即MCE并非必然受到激励失灵的困扰。现在让我们转向讨论毛泽东主义对中国农民的阶级分析以及主流文献中一些代表性的经验研究,以阐明MCE究竟如何可能避免激励失灵,以及主流文献中用以证明这种固有激励失灵的经验证据实际上可能证明了相反的结论。²⁰
正如已经表明的那样,新古典主义的“经济人”观点利用搭便车模型来论证MCE注定会失败。在此过程中,它强调农业的某些特殊特征,例如零散的工作场地和漫长的生产周期,在打破报酬与劳动之间的联系以及提高劳动监督成本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从新古典主义观点分析,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差异似乎更多的是程度问题而非性质问题。新古典主义搭便车模型的核心是“经济人”假设,而不是农业与工业之间的程度差异。在集体耕作下,只要农民仍然是自利的理性计算者,即使农业变成工业(即工作场地更加集中,生产周期更短),报酬-劳动联系和劳动监督仍将存在问题——可能改变的只是问题的严重程度。
毛泽东思想为理解人性和农民的激励取向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它以生产方式和阶级分析为中心来分析农民,这与新古典主义搭便车模型中固有的理性主义、个人主义方法截然不同。从历史唯物主义(Maoism从中汲取思想)的观点来看,农民的激励结构不能从任何先验假设中推导出来,而必须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一系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加以把握。
毛泽东分析的出发点是解放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普遍存在的小农生产方式(一种小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早在20世纪20年代,毛泽东就已注意到,在这种生产方式下,中国农民分化为几个不同的社会阶级: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贫农和农村无产阶级(毛泽东 1926)。到了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继续这一分析思路,并使用了一套略有不同的术语: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工人(毛泽东 1933)。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将这种对农民的阶级分析应用于考察不同农村社会阶级对集体化运动的态度。
“在广大的农村人口中,贫农、新下中农和老下中农,对于走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很大的积极性,他们积极地响应党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号召,特别是那些政治觉悟较高的分子。这是因为贫农的经济生活是困难的,下中农的经济生活虽然比解放以前有所改善,但是也还很困难,或者说,也还不够富裕。……对于他们说来,唯一的道路就是团结起来,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共同富裕起来。除了这条道路以外,没有第二条道路可以使他们摆脱贫困和困难的地位,也没有第二条道路可以使他们抵抗像今年这样全国范围内的大水大旱的灾荒。”毛泽东非常清楚,农民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分化为具有不同经济地位和主张的阶级。这一观点与新古典主义的假设形成鲜明对比,后者认为所有农民都具有相同的经济地位,共享相同的理性计算心态,并倾向于相同类型的生产关系——家庭农业。毛泽东制定了依靠贫下中农的明确战略,他相信这些农民为了摆脱困境而赞成社会主义集体农业,以促进集体化运动。值得注意的是,现有文献中那些赞同新古典主义观点的著作,在声称毛泽东时代的集体由于其“经济人”假设推导出的所谓搭便车问题而注定失败时,根本没有涉及毛泽东主义观点的这一核心支柱。
另一方面,毛泽东并未将占农民大多数的贫下中农视为铁板一块。他也清楚中国农村这两个社会阶级中不同个体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他评论道(毛泽东 1955a,第193页):
“一部分贫农和下中农,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他们的热心程度各个不同,有些人是很热心的,有些人暂时还不大热心,有些人则取了观望的态度。对于所有这些虽然是贫农或者下中农、但是暂时还不愿意加入合作社的人,应该用一段时间去教育他们,应该耐心地等待他们,不要违反自愿原则,勉强地把他们拉进来。”
除了集体化应依赖于中国农村何种社会阶级基础的问题外,毛泽东还讨论了谁来激活这一社会阶级基础的政治领导问题(毛泽东 1955b,第210页):
“第一,依靠党员和团员。……
第二,依靠党外广大的贫农和下中农的积极分子,这些积极分子应当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五左右(例如一个二千五百人的乡,应当有一百二十五个这样的积极分子)。我们必须努力培养出一批这样的积极分子,而且不应当把他们和群众混同起来。
第三,依靠广大的贫农和下中农两个阶层的群众。”
总之,毛泽东并不认为农民中的不同成员具有相同的人性或对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的激励取向。在他看来,政治领导与群众之间的差异,农民中不同社会阶级之间的差异,以及支持集体化的社会阶级中个体之间的差异,都存在并且对于设计和实施制度和政策至关重要。相比之下,新古典主义观点基本上将所有农民成员都视为同质的、自利的理性计算者,这为其声称毛泽东时代的集体遭受激励失败提供了支持。
基于前面对现有文献中相互竞争的观点(主要是新古典主义经济人观点和毛泽东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考察,本文对毛泽东时代集体的运作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在我看来,毛泽东时代的集体运作在一个复杂、细致的激励基础上,其中三种不同类型的工作激励并存。1962年人民公社向队组农作阶段的过渡,为三种激励因素中的一种占据主导地位提供了有利条件,这在润滑毛泽东时代集体经济的齿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理论上讲,在毛泽东时代的集体领导下,可能存在三种主要类型的工作激励。它们可以分别称为集体主义激励、个人主义激励和搭便车激励。集体主义激励的特点是为集体利益而努力工作,而不要求相应的精确回报(即不斤斤计较分配,除非是故意剥削的情况)。个人主义激励的定义是为互惠回报而工作(即如果集体产品的分配份额与自我感知的个人贡献不完全匹配,工作积极性就会受损)。搭便车激励的定义是恶意怠工和故意占有他人劳动成果。
毛泽东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可以产生的一个洞见是,这三种激励类型分别对应于小资产阶级农业生产方式下的三组社会阶级——贫下中农(或无产者和佃农)、自耕农、以及富农和地主。贫下中农由于缺乏必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工具、役畜等)或必要的劳动力,倾向于有兴趣集中各自可用的生产力要素并从事集体耕作。²¹自耕农通常可以依靠自己的私有生产资料维持生计,因此倾向于自力更生。富农和地主拥有大量生产资料,习惯于剥削贫下中农,所以如果他们被迫加入集体,他们会倾向于占别人的便宜。
这并不是说新古典主义观点对于分析毛泽东时代集体的激励结构毫无用处。仔细考察后,我们可以发现新古典主义观点实际上是毛泽东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一个子集或特例,因为“经济人”假设既可以应用于自耕农阶级,也可以应用于富农和地主阶级。然而,我们需要注意到这两组社会阶级在搭便车行为上的一个重要区别:富农和地主倾向于进行主动的或故意的搭便车行为,而自耕农则倾向于进行被动的或反应性的搭便车行为,即他们倾向于以自己的怠工(或感觉工作积极性降低)来回应怠工行为或自认为不公平的分配结果。²²
必须澄清的是,这三种激励类型都是理想类型。某个特定社会阶级的特定成员并不一定属于与该特定社会阶级相对应的激励理想类型。例如,一个贫农更有可能根据集体主义激励行事,但无法保证此人也不受其他两种激励类型的影响。笔者强调社会阶级地位对工作激励的影响的重要性,但并不认同任何将此逻辑推向决定论极端的观点。具体而言,一个贫农既可能受到其自身阶级地位的影响,也可能受到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制度环境和其他人影响的影响。因此,与其他社会阶级相对应的激励类型,以及商品交换不断再生产的商品拜物教文化,都可能动摇甚至主导这个贫农原有的特定阶级的工作激励。但总的来说,可以公平地说,在一个普通贫农的激励结构中,集体主义激励比其他两种激励类型更具分量。同理,一个普通自耕农倾向于根据个人主义激励行事,尽管可能受到集体主义和搭便车激励的影响。以此类推。
1962年,为了应对大跃进饥荒——这是几种不同因素共同作用造成的悲剧性后果,其中一个因素是由于缺乏行政管理经验和工作积极性不足而导致管理大规模核算单位的巨大困难——毛泽东时代的集体经济在其治理结构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公社内部最低一级的生产单位,即生产队(简称队),稳定成为基本核算单位。此前,人民公社内部另外两个更高级别的生产单位,即大队和公社,曾是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的级别通常涵盖一个自然村或一个村庄邻里的区域,而大队的级别则涵盖一个行政村的区域,公社的级别则涵盖一个乡镇的区域。这种差异不仅是地理或行政上的,更重要的是,它也是社会或组织上的。同一生产队的成员通常是亲戚或近邻。他们生活在同一个互动密切的社区,彼此非常了解。在某种程度上,一个生产队或一个自然村,更像一个大家庭,而不像一个市场化的社会。
从现有文献中的新古典主义观点来看,人们可能会解释说,通过将基本核算单位的级别从公社或大队下调到生产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层实际上承认了利他主义意识形态的破产,并屈服于农民的人性或以自身利益为导向的工作激励。这种解释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因为如果大队或公社是基本核算单位,大多数农民会被对陌生人的不信任所压倒,并倾向于按照个人主义激励行事,从而导致搭便车问题。
然而,总的来说,这种解释具有误导性,因为随着生产队成为基本核算单位,大多数农民会更倾向于按照集体主义激励行事,而不是刺激个人主义激励。
本博士论文认为,从劳动激励的角度来看,队组农作(即在毛泽东时代集体农业中,队是基本核算单位)的性质是一种鼓励和发展集体主义激励至其最大潜能的制度形式。下一段将通过运用历史证据,特别是来自现有文献中案例研究的证据,来论证这一论点的有效性。
本节的核心论点是,激励失灵并非毛泽东时代集体经济(MCE)所固有的;相反,在毛泽东时代的队组农作制度下,存在着一套重要的有利条件,使得集体主义激励能够在有效激励农民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更具体地说,在三种工作激励类型中,毛泽东时代的队组农作制度为惩罚搭便车激励、约束个人主义激励以及利用集体主义激励提供了制度条件。
鉴于这一论点似乎与现有文献中的新古典主义观点相反——后者认为毛泽东时代的集体因徒劳地试图改变农民的“经济人”心态而遭受固有的激励失败——那么很自然地会假设,代表新古典主义观点的著作中提出的经验证据将构成本节核心论点的有力反驳。因此,为了以最有说服力的方式证明核心论点的有效性,我将完全依赖这些材料来考察毛泽东时代队组农作中工作激励的运作情况。
新古典主义观点著作中汇集的经验材料主要基于案例研究。本文将主要考察以下代表性案例研究的历史证据:弗里德曼等人 1991,李 2005,安戈 1985,张江华(Zhang Jianghua)2007,以及张乐天 1998。
对这些材料的考察并非按照前述案例研究的顺序列出,而是围绕三种激励类型进行主题化组织,以便突出它们各自如何受到毛泽东时代队组农作制度的影响。
从毛泽东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地主和富农阶级的成员是最倾向于采取搭便车激励行为的人。新古典文献由于其所信奉的特定理论视角,通常不会有意识地追溯那些倾向于搭便车或懒惰的农民的社会阶级归属,但在这类文献中仍然可以找到证据表明,毛泽东时代的队组农作提供了充分的制度机制,或多或少有效地将故意的搭便车行为控制在最低限度,至少肯定没有达到不受控制或对集体农业致命的程度。
根据张江华2007年的研究,“懒人”,或者说故意采取搭便车激励行为的农民,仅占生产队总成员的不到10%(张江华 2007,第7页)。张还指出,他们的搭便车激励可能来自多种多样的原因,包括一些特殊的个人情况(未婚或体弱)。张评论说,这种搭便车激励不具代表性,因为它给采取这种行为的人带来了巨大的代价——丧失自尊。还值得注意的是,张将地主和富农阶级成员身份列为搭便车激励的来源之一。(张江华 2007,第8页)在这方面,张江华2007年的研究是新古典文献中的一个例外,后者通常避免讨论社会阶级问题。
李2005年讨论了领跑者的作用,即一个工作节奏快的人,在迫使节奏慢的人更努力工作方面的作用。具体的心理效应是复杂的。一方面,“一个工作太快或太认真的人可能会成为他人嫉妒或怨恨的目标,因为队长会用他或她作为模范工人和领跑者。”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的工作质量不比其他人差,队员们可以容忍他远远领先于其他人。”(李2005,第90页)领跑者可能在节奏慢的人身上引起的嫉妒或怨恨表明,领跑者可能产生的榜样效应确实存在,否则节奏慢的人就不会“恨”他或她。当领跑者不是出于自身利益而是出于利他主义或政治领导角色行事时,这种榜样效应会更强、更积极。有理由相信,在一个团队的所有成员中,一定比例的人或多或少是利他的,他们愿意充当领跑者。如果队长本人就是领跑者,这种榜样效应会更强。对此没有保证,但毛泽东时代的队组农作至少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队员之间的相互监督也是毛泽东时代队组农作制度促进的一个重要因素,它防止了搭便车激励的蔓延。由于生产队的规模相对较小(远小于大队或公社),即使一个人怠工,也可能对集体产品(即人人共享的收入池)造成不可忽视的损害,更不用说大部分队员怠工了。因此,即使不具备高度的利他主义,仅仅出于自身利益,生产队的成员也会有强烈的动机去监督彼此在集体耕作中的劳动努力。
李2005年描述了这种“队员之间的相互竞争和监督”效应:“一起工作时,村民们总是密切关注彼此,以便了解其他人做了多少以及做得如何……如果一个队员工作过于粗心却得到与其他队员相同的工分,大多数队员都无法接受……这种同伴压力在同龄组或同劳动等级的人群中尤其强烈。”(李2005,第90页)
新古典文献受其“经济人”假设的影响,往往忽视集体主义激励的存在。因此,通常很难在新古典主义观点的著作中找到揭示集体主义激励作用的经验证据。尽管如此,笔者还是设法找到了一些这样的证据。
在处理队长监督与普通队员劳动积极性之间的关系时,李引述了普通队员的感受:“他们没有感受到来自队长的任何压力,因为队长在他们工作时大多不在场;他们按照自己对如何正确做事的‘自觉’(zijue)来完成工作。”(李 2005,第91页)。这里的“自觉”可以解释为集体主义激励。李进一步谈到了一位典型队员认为这种“自觉”从何而来:“生产队是他或她收入的主要来源;生产队的状况直接影响所有成员的福祉。换句话说,队长与队员之间的关系不同于雇主与雇员或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他们都属于同一个集体,共享他们合作劳动的成果。双方都必须为共同利益负责。”(李 2005,第91页)这就是说,毛泽东时代的队组农作确实在队员之间提供了一种共同利益感,这塑造了他们偏向集体主义激励的劳动积极性。
弗里德曼等人1991年的研究描述了一个由四个贫下中农²³家庭组成的土地入股合作社,并叙述道,最初“村民们嘲笑几个贫弱家庭能够抱团的想法”,并认为“争吵会导致一场不可能的冒险迅速瓦解”。(弗里德曼等人 1991,第61-2页)但结果是这个合作社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功。“工作非常辛苦,但到农忙年结束时……合作社每亩223斤的产量远高于贫困村民通常在旱地上获得的收成……接近拥有优质土地和牲畜的富裕个体农户的产量。”(弗里德曼等人 1991,第65页)作者评论说,取得这一成功的诸多原因包括:“这个团体很小。成员们是朋友和邻居。没有人感到吃亏,因为大家都缺劳动力……当需要做决定时,小组可以当场讨论。耿长锁(Geng Changsuo)务实、能干、诚实的领导也至关重要。”(弗里德曼等人 1991,第65页)必须指出,这个土地入股合作社代表了集体化运动的第二阶段(即初级农业合作社),它与毛泽东时代集体经济的生产队阶段不同,但在核算单位的规模上与后者相似——一个相对较小的邻里,农民们彼此熟悉,并具有相当程度的社会信任。弗里德曼等人提供的上述描述表明,集体主义激励并非脱离经济现实的意识形态说教。正如毛泽东所评论的那样,贫下中农深知只有通过在集体农业中集中他们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他们才能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因此,他们确实拥有在集体农业中努力工作的强烈动机,并且他们知道他们是为了实际的经济利益而努力工作,而不是因为一些空洞的言辞(即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统一是真实的)。
张乐天1998年提到,在某些情况下,生产队会表现出高度的劳动积极性:“例如,在由大队、公社或县组织的兴修水利工程活动中……营造了一种‘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下,整个生产队的荣誉感和‘面子’因素会刺激参与者的劳动积极性。”(张乐天 1998,第352页)此外,在日常生产活动中,当生产队将任务分配给几个作业组时,这些作业组会自动形成一种竞争氛围,属于某个特定作业组的农民会非常努力地帮助自己的作业组尽快完成分配的任务。张评论说,“这种类型(队组农作管理)的劳动效率甚至可能超过任务承包到户时所能达到的劳动效率水平。”(张乐天 1998,第353页)尽管张乐天1998年的著作总体上试图将毛泽东时代的集体经济定义为激励失败的案例,但这两个描述非常清楚地表明,无论是在由更高级别(大队及以上)组织的活动中生产队之间相互竞争时,还是在一个生产队被划分为几个相互竞争的下级小组时,生产队确实能够为农民提供足够的劳动激励。对自己生产队或小队组集体经济利益的共享感及其产生的集体荣誉感,构成了集体主义激励的坚实基础。
毛泽东时代集体中“按需分配”与“按劳分配”并存的现象,通常被新古典文献用来论证毛泽东时代集体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然而,在安戈1985年的研究中,可以找到有力的证据表明,“按需分配”确实受到大多数农民的青睐,而且它是建立在几乎每个人都需要将风险降到最低的基础之上的。安戈1985年讨论了大跃进运动之后毛泽东时代集体经济与家庭经营之间的反复变化。1961年,家庭经营得以恢复,但它“然而,并没有特别服务于那些孩子太小不能工作,或者丈夫体弱多病或不善于农业规划的家庭的利益。”(安戈1985,第120页)因此,当后来政府要求恢复毛泽东时代的队组农作时,“正是陈家村(Chen Village)的贫困户欢迎政府的要求。”安戈继续叙述道,“即使是较富裕的家庭也顺从了,没有出现任何抱怨”,因为“无论某对夫妻多么强壮能干,他们自家小块土地遭受虫害、断腿或意外疾病的可能性都时刻存在……陈家村人,像其他地方的农民一样,想要的不仅仅是最大限度地增加收入的机会;他们还想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安戈1985,第120-1页)
最棘手的情况是个人主义激励。即使从毛泽东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这种激励在所有三个主要的社会阶级群体中都表现活跃。它无疑是自耕农或中农激励结构中的主导因素,但它也可能影响中国农村其他两个社会阶级群体,特别是贫下中农,因为每个人都生活在商品交换的更大环境中,这种环境在日常生活中强化了等量劳动等价交换的心态。
在这方面,对贫困和中农影响最大的集体主义激励并不意味着所有这些农民都愿意为了集体农业而无私奉献,而不顾自身的经济利益。少数具有高度自觉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锋队”相信利他主义,他们可以从贫下中农(甚至在某些条件下,从其他两个社会阶级群体中,例如毛泽东本人)中发展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普通的贫农或下中农也会信奉利他主义。因此,利他主义主要在先锋队员作为榜样无私努力工作以激励其他非利他主义农民效仿时发挥作用。在没有这种先锋队的情况下,正如上文所讨论的,集体主义激励的正常类型主要源于这样一个事实:贫下中农(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属于其他社会阶级的农民)坚定地寻求在集体农业中集中他们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以改善他们自身的经济状况。在这个程度上,集体主义激励可以被解释为个人主义激励的一个开明变体。
个人主义激励与集体主义激励之间的区别,正如已经讨论过的,并非利他主义与自私自利之间的区别,因为利他主义(中文为“损己利人”,即牺牲自己利益他人)是集体主义激励的一种极端情况,而自私自利(中文为“损人利己”,即牺牲他人利益自己)更多时候指的是搭便车激励。在正常情况下,个人主义激励和集体主义激励都指的是在平等基础上互惠互利的心态(中文为“利己利人”,即既利于自己也利于他人)。在它们之间,用做饼和分饼的比喻来说,个人主义激励强调严格按照劳动贡献分饼,以便个人能够绝对增加其经济利益,即侧重于通过精确划分相对份额来增加个人的绝对经济利益。另一方面,集体主义激励则强调维护集体大饼的存在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做大这块饼,即侧重于通过自身的努力工作来参与并增加集体总利益,从而增加个人的绝对经济利益,也就是说,只要不被故意搭便车的他人恶意占便宜,就不会对精确的分配斤斤计较。
毛泽东时代集体(集体耕作和集体分配)的关键经济活动使得集体主义激励和个人主义激励之间的这种细微差别变得更加重要。尽管关于新古典主义对毛泽东时代激励失败的理论推理和证据存在问题,但新古典主义著作中经常提出的主张,即在集体耕作中不可能存在个人劳动贡献与个人在集体总产品中所占份额之间的精确联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24然而,这一事实的含义仍然是开放性的:如果这种联系在毛泽东时代的集体中不可能存在,应该怎么办?
在提出应该怎么做之前,人们应该知道如何解读这一事实。笔者认为,这一事实的本质最好被解读为精确的劳动-报酬联系与毛泽东时代的集体之间的不相容性,即有毛泽东时代的集体,就没有精确的劳动-报酬联系;反之,有精确的劳动-报酬联系,就没有毛泽东时代的集体。在我们清楚了这一事实的本质之后,就更容易确定关于应该如何处理这一问题的两种截然相反的建议。一种建议是,用家庭耕作取代毛泽东时代的集体,以便建立精确的劳动-报酬联系。这种解决方案符合新古典主义的观点。另一种建议是,放弃精确的劳动-报酬联系的想法,以便毛泽东时代的集体能够有效运作。这第二种解决方案符合本文提出的核心论点,或者说导向本文的核心论点。
要以第二种方案的方式解决这种不相容问题,即在放弃建立精确劳动报酬联系的目标的同时保留毛泽东时代的集体,就需要对劳动报酬联系有更复杂的理解,因为人们不能将劳动报酬联系视为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除非每个人都变得具有利他主义思想,而这是不现实的。
笔者认为,集体耕作下的劳动-报酬联系是一个程度问题,而不是精确性问题。如果在集体耕作下,劳动与报酬之间永远不可能存在精确的联系,那么每个农民都会承认这个事实。如果每个人都承认这个事实,那么在分配时,每个人都不会要求劳动与报酬之间的联系必须精确。这很容易理解:如果无法建立精确的劳动-报酬对应关系,那么任何农民自我感知的劳动-报酬联系本质上都必定是主观的甚至是带有偏见的。你认为你的劳动贡献占最终总产品的10%,但如果你的一个队友认为它是9%呢?在一个生产队内部通常存在足够的社会信任,所以意见分歧主要在于对具体事实的具体判断。每个农民都应该明白,自己对具体事实的判断可能与具体事实不符。因此,同一个生产队的成员在聚集讨论应得的集体总产品相对份额时,他们头脑中现实地会有一个价值范围,而不是一个单一的价值。这个价值范围也可以理解为容忍度。范围越宽,当别人不同意你自我感知的相对份额时,你的容忍度就越高。
而且,与单一价值相关的容忍度肯定低于与一定范围值相关的容忍度。因此,只要农民知道这种不存在性,并旨在用自我感知的模糊的可能分配份额范围取代自我感知的精确分配份额值,那么精确的劳动-报酬联系的不存在就未必会导致毛泽东时代集体的激励失败。如果这种模糊范围能够变得更加模糊或更宽,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将会进一步提高。
这种关于劳动-报酬联系(精确的或模糊的)的讨论与个人主义激励和集体主义激励之间的区别有何关系?正如上文所总结的,个人主义激励的特点是要求精确区分个人劳动贡献,即侧重于以绝对公平的方式分割集体大饼,而集体主义激励的特点是优先维护和扩大集体大饼,以此作为保障和增加个人利益的方式。因此,个人主义激励倾向于要求精确的劳动-报酬联系,而集体主义激励则倾向于采用模糊的劳动-报酬联系。
显然,为了使毛泽东时代的集体能够生存和繁荣,个人主义激励必须受到抑制,而集体主义激励必须得到提倡。毛泽东时代队组农作制度下农民心理的一个重要事实,有利于抑制个人主义激励,从而巩固毛泽东时代的集体。这个事实是,生产队的规模相对较小,有利于其成员之间发展社会信任。
上文已经讨论过,在毛泽东时代的队组农作制度下,没有必要建立精确的劳动-报酬联系,这种联系无论如何也无法做到精确,因为农民可以接受模糊的劳动-报酬联系并按照集体主义激励行事。在本段中,笔者将重点讨论问题的另一面,即如果在毛泽东时代的队组农作制度下努力使劳动-报酬联系精确化,或者换句话说,如果诉诸而非压制个人主义激励,将会发生什么?
理论上讲,答案应该很清楚。由于劳动-报酬联系无法做到精确,任何试图使其精确化的努力都会导致更多时间用于设计复杂的工分制度,增加劳动质量监督的难度,提高对相对分配份额的敏感性,降低队友之间对个人劳动贡献不同看法的容忍度,以及可能降低集体士气水平。总之,试图建立精确的劳动-报酬联系会释放个人主义激励,这可能会损害队员之间健康的合作关系,并降低集体耕作的劳动效率。
由于新古典主义信条的普遍影响,即农民渴望精确的劳动-报酬联系,而毛泽东时代的集体耕作无法建立这种联系,现有文献中关于在MCE下为使劳动激励发挥作用而进行的各种努力(通常收效甚微或毫无效果)的案例研究,很容易被解读为支持MCE激励失败的论点。然而,仔细审视后,笔者发现,如果以不同的方式,即符合本文核心论点的方式来解读这些历史叙述,人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它们。
最好的例子是安戈1985年的研究,它描述了陈家村效仿大寨(Dazhai)模式的过程和结果。最初,陈家村的农民怀着对“政治态度”(即关心集体利益)的良好信念,取得了惊人的生产增长。然而,后来大寨的群众评议机制导致了对集体收入中个人相对份额分歧的过度敏感。将政治态度纳入工分和集体分配的决定最终与其最初的期望背道而驰。即使在将政治态度从报酬方案中移除后,陈家村村民的士气和劳动积极性仍然无法恢复正常状态,因为社会信任已经受到损害(安戈1985,第122-34页)。
这段叙述可以从以下方式解读,以证明MCE下的激励问题并非固有的,而很可能源于对精确劳动-报酬联系的追求。首先,最初效仿大寨模式的成功表明,陈家村的农民确实具有集体主义激励。其次,“学习大寨”的下坡路实际上涉及两个步骤。第一步是将政治态度纳入工分确定体系,即将精神动力转化为物质/金钱激励。这为以牺牲集体主义激励为代价促进个人主义激励铺平了道路。第二步是寻求精确劳动-报酬联系的诱惑,表现为在群众评议会上就彼此分配给政治态度的确切工分发生分裂性争吵。正是通过这两个步骤,集体主义激励逐渐让位于个人主义激励,导致了劳动积极性不足的问题。
如果政治态度像陈家村村民在学习大寨的最初几年那样,作为一种定性的、精神的工具来加强集体主义态度而保持有效,那么最初的巨大成功很可能应该持续下去。在政治态度成为更复杂的工分评级体系的基础的一部分之后,它不仅停止了促进集体主义激励的作用,而且还增强了个人主义激励,因为它与可量化的劳动贡献相结合,增加了陈家村村民对集体产品份额相对百分比的敏感性。因此,激烈的争吵、怠工、搭便车等现象随之而来。这个过程一旦启动,就会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即使在政治态度从工分评级体系中移除后,它也根本无法轻易停止。
李2005年的研究也包含了将大寨模式应用于江苏省(Jiangsu Province)秦村(Qin Village)的记述,这与将政治态度转化为严格执行的可量化机制以促进个人主义物质激励是失败真正根源的解释是一致的。用李的话说,“大寨制度在开始时是有效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村民们因相互评价基本工分而发生争吵。”(李2005,第92-3页)
中国农村其他村庄在多大程度上忠实地遵循了最初大寨模式的精神,在此并非真正关注的问题。最初的大寨模式究竟是什么样子——金钱奖励是否与政治态度挂钩,群众评议是否在影响分配结果方面发挥了实质性作用等等,也不是重点。本博士论文并不试图为大寨模式辩护。相反,它试图揭示在何种条件下MCE可以使激励发挥作用。大寨的做法可能并非大寨本身所能达到的最佳状态,更不用说大寨行之有效的方法在其他村庄可能行不通的可能性了。即使大寨确实将金钱奖励与政治态度挂钩,并且确实认真对待群众评议,而且,即使这两个机制成功地解决了大寨的激励问题,也并不意味着陈家村就应该照搬大寨的做法才能使激励发挥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陈家村在效仿大寨模式之前曾经采用的定额计酬法可能具有一定的持续影响,这很可能在将最初对政治态度的关注转变为最终对精确劳动-报酬联系的追求方面起到了作用。
政治态度,最初作为促进集体主义激励的道德因素,在陈家村和秦村被转化为额外的物质刺激以强化个人主义激励,这一事实可以与另一个有趣的心理学发现相提并论。格尼齐(Gneezy)和鲁斯蒂奇尼(Rustichini)2000年记录了一项关于父母从日托中心接孩子的实验。观察结果是,当因迟到接孩子而被罚款时,父母会更倾向于选择迟到并支付罚款。这表明,当一种道德价值(如果父母因迟到而不被罚款,而是友好地提醒他们准时的重要性,他们会出于道德内疚感而努力避免迟到)被一种物质激励(当因迟到而被罚款时,接孩子就变成了一个市场,罚款可以换取迟到的时间)所取代时,反应可能会导致更糟糕的结果。换句话说,将道德激励转化为物质激励的努力可能会降低激励的力量。
第二类促进个人主义激励的努力(第一类是前述将政治态度转化为物质激励,如安戈1985年的陈家村和李2005年的秦村学习大寨模式的方式所示)是探索更复杂的工分制度的任务定额(主要是时间定额和计件定额)形式。在这方面,李2005年和张江华2007年的研究产生了一些有趣的观察。他们发现,时间定额和计件定额形式各有其优势:时间定额适合对工作质量要求较高的农活,而计件定额则适合涉及低技能、高强度苦力活的农活。尽管这两种形式各有其专门的应用领域,但并非所有农活都能如此清晰地分类。此外,这两种形式在劳动激励和劳动监督方面都存在固有的缺点:时间定额形式更容易导致怠工或“出工不出力”,而计件定额形式则倾向于导致农民追求数量而牺牲工作质量。(李2005,第92页;张江华2007,第19页)
工分制度中任务定额形式的这些局限性,对生产队领导层的管理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增加了劳动监督的难度和成本。这表明,在毛泽东时代的集体内部追求精确的劳动-报酬联系,总是会受到经济资源浪费、效率损失以及农民之间激励摩擦加剧的影响。当然,这并不自动意味着用家庭经营取代毛泽东时代的集体就会增加农业生产,因为追求精确劳动-报酬联系的破坏性影响可能仍然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并且也可能被队组农作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所抵消。对此的详细讨论超出了本研究的范围。
就本研究而言,关于时间定额和计件定额形式局限性的讨论的含义是,仅仅因为努力使劳动-报酬联系精确化未能刺激劳动积极性,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时代的集体注定会遭受激励失败。相反,它可以指向相反的方向:当促进集体主义激励并使个人主义激励沉睡时,毛泽东时代的集体将会发挥作用。25人们至少应该意识到这种可能性,并思考这个问题是否可以被视为在这两种安排之间取得令人满意的平衡的问题。
2.2.1.2.2 毛泽东时代集体经济的激励绩效
毛泽东时代集体经济(MCE)并非必然导致无法弥补的激励失灵是一回事。而在MCE下,激励问题有多普遍和严重则是另一回事。上述分析表明,即使激励失灵并非MCE所固有,缺乏劳动积极性的问题确实在MCE下发生过。人们当然可以争论应该采取何种解决方案来纠正缺乏劳动积极性的问题(即在取消促进个人主义激励的精确工分计量做法和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HRS)取代MCE这两个选择之间),但只要激励问题在MCE下发生过,用HRS取代MCE的想法至少在HRS制度确实消除了确定集体产品中个人份额的必要性方面,似乎总是有一定道理的。因此,思考在MCE下激励问题有多普遍和严重的问题也很重要,无论其原因是否是MCE固有的。
这里必须指出,在主流文献中,令人惊讶地缺乏在全国范围内讨论这个问题的著作。能够找到的只有那些要么依赖搭便车模型从理论上、抽象地断言MCE下存在激励失灵的著作,要么利用个别村庄层面的案例研究来揭示有限地区激励问题的著作。全国范围内的证据确实难以获得。但是,笔者能够收集到的有限经验材料,即前文已经讨论过的那些材料,并不能为MCE下的激励问题在中国各地农村集体中普遍存在的结论提供经验支持。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最终覆盖了中国99%以上农村地区的“一刀切”式的去集体化运动将是一个糟糕的想法和实践,因为从激励角度看,它对整个中国农村并非必要,而从规模经济角度看,它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损害。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个基本事实,即在去集体化运动之前(也就是中国政治风向从亲毛泽东转向亲改革之前),关于MCE中劳动激励的主流观点是高度积极的,这一点在1975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考察团的以下记述中得到了明确体现:
访问中国的人不能不为中国农民坚持不懈地进行生产劳动所打动。人们很难抵制将中国成千上万的人以稳定、轻松但有目的、有成效的步伐劳动的景象——以至于田野常常看起来更像是工厂车间——与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经常看到的无精打采的闲散人群进行比较的诱惑。这现在已是一个有充分文献记载的事实,访问者从中国回来后,经常被问到:是什么让中国农民如此努力工作?(联合国粮农组织 1978,第44页)
其次,在现有文献中,有三篇关于在MCE下经营良好和经营不佳的农村集体相对比例的记述,所有这些记述都表明,至少有相当一部分农村集体在MCE下经营良好。由于这类研究在现有文献中通常难以找到,而且这个问题对于本博士论文的目的极为重要,请允许我详细引用以下这三篇记述。前两篇记述来自韩丁,一位国际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在中国农村拥有广泛的田野调查经验。
一群年轻的经济学家在1980年告诉我,他们所做的导致改革的分析表明,大约30%的村集体经营良好,另外30%经营得很差,中间剩下的40%可以说既不繁荣也不崩溃,面临许多问题。根据这些信息,人们可以做出各种陈述。人们可以将底部的30%和中间的40%加起来,说大多数经营不善。人们可以将顶部的30%和中间的40%加起来,说大多数至少是可行的。或者人们可以说,成功和失败大致相当(顶部和底部的30%),而好坏参半的结果占主导地位(中间的40%)。(韩丁1990,第140页)
七十年代末,中央委员会农业政策研究小组进行的全面研究得出结论,30%的集体村庄经营良好,40%面临严重问题但仍能维持,另有30%经营非常糟糕,难以重组。(韩丁1994,第3页)
第三份记述来自李友久(Youjiu Li),一位前农业部副部长,他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参与了中央领导层关于去集体化的讨论和决策。
当时农业部有一项调查,结果是三分之一的生产队搞得很好,中间的40%搞得还可以,大约四分之一搞得不好……杜(Du)润生最初反对全盘去集体化的想法,主张保留那三分之一好的生产队……但他看到万里(Wan Li)的态度后就让步了,成了最积极支持全盘去集体化的人。他最初主张保留三分之一的生产队,或者至少保留四分之一以便进行比较。(李友久 2003,第3-4页)
这三份记述的共同之处在于,有相当比例的农村集体(30%至三分之一)经营良好,而经营不善的农村集体比例并非多数(25%至30%)。中间是40%的农村集体,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尚能维持。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底层25%至30%的集体和中间40%的集体而言,困扰它们或它们面临的问题未必涉及劳动激励问题。但鉴于劳动激励可能是最大的问题之一,也可能是农村集体经营其他方面的结果或原因,为简单起见,假设所有底层和中间集体经营不善或面临问题都是因为激励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
但即使情况如此,也不意味着所有农村集体都应该去集体化。当然,顶尖的30%到三分之一的集体应该保留。即使是中间的40%也应该给予更长的时间和机会进行进一步的试验和改进,至少当地集体成员应该有选择的自由(在MCE和HRS之间)。杜润生在上述第三个记述中最初赞成的观点,即至少应该保留顶尖的集体,似乎是一个合理的提议。然而,相比之下,去集体化作为一场自上而下、强制性的、“一刀切”的运动来实施,肯定不适合顶尖30%到三分之一集体的具体情况,也可能不适合中间40%集体的具体情况。
另一项表明MCE并未受到激励失灵困扰的证据来自粮食产量数据。
如果像中国政府经常声称的那样,以及从现有文献中的传统观点推断的那样,MCE普遍存在激励失灵,而HRS将中国人民从永远无法养活自己的失败中拯救出来,那么MCE下的粮食生产(这是毛泽东时代中国最重要的农业任务)将会失败,或者至少远不如HRS下的粮食生产。这正是中国政府一直试图让公众相信的,即HRS在粮食生产方面远优于MCE。在一系列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关于中国社会经济成就的统计报告的第一篇中,尽管同一篇文章中给出的数字实际上表明了相反的情况,中国统计当局仍将后毛泽东时代的粮食生产增长率描绘得远高于毛泽东时代(中国国家统计局 2009c)。利用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我制作了表2.4,以比较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粮食生产记录。


表2.4清楚地显示,就粮食生产年均增长率而言,MCE的表现优于HRS。由于1962-1978年期间包括了几年恢复期(1962-1966年),因此将1966-1978年或1952-1978年视为毛泽东时期可能更为准确。毫无疑问,MCE的表现优于HRS(1966-1978年为2.99%,1952-1978年为2.41%,而1978-2007年为1.73%)。从表2.5可以看出,关键年份1952年、1966年、1978年、1983年和2007年并非局部高点或低点,可能受到极端天气条件或其他因素的影响(1984年是局部高点,因此选择1983年)。
有人可能会争辩说,HRS下的粮食生产受到农业活动多样化以及由此导致的粮食播种面积萎缩的影响,表中显示的1978年至2007年粮食播种面积的下降确实证实了这一点。为了考虑这一因素,还计算了关键年份的粮食单产数据以及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粮食单产的年均增长率。这些数据仍然清楚地表明,就粮食单产的年均增长率而言,HRS的表现不如MCE(1978-2007年的2.2%小于1952-1978年的2.53%,或1966-1978年的4.69%)。就粮食产量的绝对增长而言,而非年均增长率,HRS时期的1978-2007年给出了一个更高的数字(196,838吨),高于MCE时期的1952-1978年(140,850吨)。然而,考虑到去集体化直到1984年才完成,可以说代表HRS的最佳时期应该是1983-2007年。如果选择这个时间范围,那么MCE的表现优于HRS(140,850吨大于114,328吨)。另一方面,有人可能会争辩说,即使HRS在粮食生产的年均增长率或绝对增长方面可能不如MCE,但如果我们看单位劳动力的粮食产量,结果可能有利于HRS。
缺乏数据来核实这一点,但笔者同意,单位劳动力粮食产量的指标可能有利于HRS,原因如下。首先,在HRS时代,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迁出中国农村以及粮食种植劳动力向经济作物部门或非农业部门转移的浪潮。这将导致中国农村每公顷粮食耕地的劳动力减少。其次,由于在HRS时期,改良种子、化肥和农药等现代工业投入品的可获得性和应用日益增加,这些现代投入品替代了劳动投入。然而,我们也应该注意到,MCE时代实际上促进了这两种力量(在第一种情况下,MCE时代的粮食生产增长使得农民能够在不担心饥饿的情况下转向非粮食生产活动;在第二种情况下,现代工业投入品以及实现这些投入品潜力所必需的其他基础设施,在MCE时代得到了良好发展,因此应被视为MCE时代遗留下来的遗产或基础)。后续关于MCE与HRS相互作用的部分将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当然,也有人可能会争辩说,HRS时代粮食生产增长较慢或增长较小,仅仅是因为在MCE时代粮食生产已经大幅增长之后,进一步增长的空间不大。笔者同意这一论点可能有一定道理。但另一方面,也有人可能会争辩说,这一点恰恰表明MCE时代在粮食生产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功。因此,那种认为MCE下的农村集体受到激励失灵困扰的传统观点根本站不住脚。
因此,对MCE和HRS时期粮食生产绩效的比较表明,MCE中的激励问题很可能并不重要。然而,MCE不必因此问题而瘫痪,也没有必要将去集体化强加于整个中国农村。可以相对有把握地论证的是,去集体化仅改善了底层25%至30%农村的激励绩效。
总之,通过用HRS取代MCE,去集体化对中国农村的农业生产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规模经济方面,对整个中国农村的影响是负面的。在劳动激励方面,对于至少25%至30%的村庄来说,影响可以说是积极的。对于顶尖的30%至三分之一的村庄,去集体化在劳动激励方面没有产生影响。对于中间40%的村庄,去集体化的影响性质不确定。总而言之,当规模经济和劳动激励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看时,去集体化的总体影响可能是负面的。
2.2.2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毛泽东时代集体经济的互动
仅仅因为在1978-1984年间中国农村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HRS)取代了毛泽东时代集体经济(MCE),并不意味着MCE的影响就完全消失了。1978年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既有变化也有延续。还应关注MCE遗留给经济改革时代的遗产。在2.2.1节中,分析的重点是HRS给中国农村带来的变化及其对中国农业生产的积极和消极影响。现在是时候讨论MCE的遗产如何影响了HRS主导下的中国农村农业生产,即自1978年以来HRS如何与MCE互动。
MCE与HRS之间的互动可分为两个时期:1978-1984年和1984年以后。1978-1984年这个第一个时期值得特别关注,因为在许多现有文献中,这个时期被含蓄地视为MCE已经消失而HRS已经确立的时期。历史上并非如此。1978-1984年是中国农村MCE和HRS并存的时期,后者的比例不断增加。由于MCE在整个时期内仍在不同程度上发挥作用,因此1978-1984年农业生产的绩效不能仅仅归功于HRS。
理论上讲,在此期间,MCE与HRS通过以下两种方式相互作用:1)在整个时期内,中国农村仍有地区和集体在实行MCE,尽管其份额在下降;2)对于已经放弃MCE的地区和村庄,MCE留下的一些遗产,例如集体生产性基础设施和现代农业投入品,仍然对农业生产产生着强烈影响。在这两种HRS与MCE相互作用的方式中,第二种在1984年后时期仍然有效。
在前一节中,已经提到去集体化是以“一刀切”的方式强加于中国农村的,而不考虑地方条件和发展水平。尽管有相当一部分农村集体在MCE下经营良好或尚可,HRS仍然在那些集体中实施。在MCE表现良好的地区和村庄,对去集体化的抵制尤其强烈,去集体化通常完成得较晚。²⁶因此,1978-1984年期间农业生产的显著增长,很可能部分归因于MCE的持续存在,MCE只是在去集体化的后期才逐渐被放弃。
在某种程度上,由于MCE和HRS的并存,有理由认为在1978-1984年期间,MCE和HRS的优势都得到了利用,这促进了这一时期令人印象深刻的农业生产绩效。
有经验案例表明,在去集体化过程中,去集体化较晚(或尚未去集体化)的单位在农业产出增长方面可能比去集体化较早(或已经去集体化)的单位做得更好。例如,在较早去集体化的省份和较晚去集体化的省份之间,较早去集体化的省份(安徽、甘肃 、广西 、贵州和宁夏 )的农业增长率中位数从1976-80年间的3.5%上升到1980-84年间的9.3%,而较晚去集体化的省份组(黑龙江、吉林和辽宁省)的增长率中位数则从3.9%上升到10.5%(布拉莫尔 2004,第124-5页)。27两种情况都出现了显著增长,但较晚去集体化的省份做得更好。
另一项证据来自地方层面。在中国北方天津市 蓟县(Ji County),1983年夏天,97.3%的村庄已经完成了从MCE向HRS的过渡,但在小麦产量实现高增长的农村中,HRS村庄的比例较低,为90.8%(赵修建(Zhao Lianjian)1989,第113-4页)。97.3%和90.8%之间的这种差异意味着,蓟县仍在实行MCE的农村集体比已经实行HRS的农村集体更有可能实现小麦产量的高增长。
这些经验证据可能导致这样一种解释,即MCE并未遭受严重的激励问题,并在某些地区(即那些较晚或未进行去集体化的地区)对农业生产做出了积极贡献。28
HRS还以第二种方式与MCE互动:从MCE年代遗留下来的遗产,例如集体生产性基础设施(如水利、土地整理、土壤改良项目)和现代工业投入品的可获得性(如化肥、杂交种子、除草剂和杀虫剂),在1978年后时期继续在促进农业生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不仅在去集体化仍在进行时(1978-1984年),而且在1984年以后的年份也是如此。
农业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或投入)与现代工业投入品(可变投入)之间存在差异。在1978年以后的年份里,农业基础设施一直在逐渐衰退:现有的未能得到良好维护,新的也很少建设。然而,另一方面,在MCE年代发展起来的现代农业投入品,在1978年以后的年份里其生产已实现商业化。
考察这样一个问题将会很有趣:如果MCE没有被HRS取代,MCE在促进现代农业投入品的生产和应用方面是否会比HRS做得更好,尽管对这个问题的任何答案都很可能仍然存在争议。让我们以杂交水稻为例。
杂交水稻是由杂交水稻种子种植的商品水稻作物,杂交水稻种子是两个基因不同的水稻品系杂交的种子。与常规水稻种子相比,杂交水稻种子具有三个特点。首先,杂交水稻种子是通过两个基因不同的亲本杂交产生的,即通过杂交育种过程,而不是近交(或自花授粉)过程,这使其区别于其他类型的水稻种子,包括在20世纪60年代“绿色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半矮秆水稻种子(仍为近交种)。²⁹其次,杂交水稻种子具有杂种优势(heterosis),这使其产量高于常规水稻种子。优良的杂交水稻品种在相似条件下比最好的近交品种增产15-20%。第三,不建议将从杂交水稻作物中收获的种子用于再植,因为由于性状的遗传分离,它们不再具有杂种优势,导致产量降低。因此,为了利用杂交水稻的益处,农民必须在每个种植季节获得新的杂交种子。(维尔马尼(Virmani)等人 2003,第3页;袁隆平(Yuan Longping)2012,第42-3页;以及巴克莱(Barclay)2007,第22页)
中国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杂交水稻研究,并在70年代初期加快了进展步伐并取得了若干决定性突破。70年代中期,杂交水稻的大规模生产成为现实。值得注意的是,在杂交水稻技术取得成就之前,中国已在改良种子领域,特别是半矮秆品种方面,于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取得了巨大进展。这与国际水稻研究所(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IRRI)取得半矮秆成就大致在同一时期,甚至可以说早了几年(朱荣(Zhu Rong)1988,第86-7页)。
中国杂交水稻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当时袁隆平在湖南省开始了他的雄性不育系试验。70年代初取得了若干决定性突破。1970年,袁隆平团队的一名成员李必湖(Bihu Li)在海南省(Hainan Province)发现了一种名为“野败(Wild Abortive)”的野生稻,为雄性不育系研究和“三系法(three-line)”杂交水稻技术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72年,“三系法”中的雄性不育系和保持系已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但尽管发明了100多个品种,恢复系的质量仍不尽如人意。
1973年,在来自东南亚³⁰稻种的帮助下,令人满意的恢复系也得以获得。这意味着“三系法”杂交水稻技术的所有遗传成分都已具备。1976年,采用“三系法”的杂交水稻品种开始在中国农村大规模种植。
1973年,即“三系法”取得成功的那一年,对“两系法”杂交水稻技术(一种代表着对“三系法”显著简化和改进的新方法)至关重要的一个水稻品种,被石明松(Mingsong Shi)在湖北省发现。这标志着中国“两系法”杂交水稻技术研究的开端。1985年,基于“两系法”的杂交水稻品种开始在中国大规模种植。³¹
MCE是促进杂交水稻技术快速进步及其在中国农村农业生产中应用的关键制度因素。在这方面,MCE的一个核心特征是将县级专业技术人员和基层(农村集体)农民技术员整合到一个地方性的杂交水稻研究网络中,称为“四级农业科研网”,涵盖县级研究所、公社级研究站、大队级研究组和生产队级研究小队。³²
这个四级网络于1969年由湖南省华容县(Huarong County)首创。在此之前,尽管建立了县级农业研究所,但科技在促进生产方面的作用并不理想。于是,县领导对湖城公社(Hucheng Commune)的一个生产队产生了兴趣,在那里,一位贫农和几名青年于1965年组织了一个研究小组,进行技术革新并将其应用于农业生产。这使得每公顷粮食产量从1964年的3825公斤增加到1969年的9195公斤(中共华容县委员会 1975,第11页)。
这个例子使县领导认识到将农业科研坚实地建立在农村集体基层成员基础上的重要性。1969年,决定建立一个覆盖县、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四级的科研网络,重点是将专业科技人员与已经是技术员或有潜力成为技术员的农村集体农民相结合。这个决定得到了相当成功的实施。例如,在该县366个大队级农业科研组中,有2722名技术员来自基层农民,平均每个科研组约有7名技术员(湖南省华容县革命委员会 1973,第8页)。这种四级科研网络迅速在湖南其他农村地区推广。到1976年,湖南省设有科研站的公社比例达到95.7%,设有科研组的大队比例达到70.5%,设有科研小队的生产队比例达到72%(湖南农业志编纂委员会 1985,第172页)。中国其他地区也效仿了华容的例子。到1975年底,中国农村建立了自己的农业科研单位的县、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的数量分别为1140个、26872个、33万个和224万个(朱荣等 1992,第573页)。
该网络对促进农业科研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产生了两个积极影响。首先,在组建中国农村农业技术人才队伍方面,该网络使专业技术人员和农民技术员相互促进,并帮助许多普通农民成为农业技术员。其次,在促进科技与中国农村农业生产相结合方面,该网络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地方农业资源,并使其面向地方农业条件和需求,从而将其转化为农业生产力的提高。
根据华容县的经验,大部分专业技术人员被派往农村集体内部的基层农业科研单位,与农民技术员和普通农民密切合作,进行与当地农业相关的研究创新。县级和公社级科研单位建立了自己的农业学校,培训来自下级的农民技术员。培训的原则是教学、科研和生产相结合,以及试验、示范和推广相结合。在1971-1973年的两年间,共培训了2200名农民技术员,并派回他们原来的集体,以促进农业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
各级科研单位还负责定期举办讲座,向普通农民普及科学知识,并组织普通农民在称为“良种田”、“试验田”和“高产田”的三类农田上从事与科学相关的农作活动。1971年,华容县有5.1万人参加了在这三类农田上的农作活动。³³
所有这些制度机制和活动都取得了双重效果,不仅将专业技术人员和农民技术员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且使技术队伍与普通农民和实际农业生产保持联系。
在袁隆平领导的团队进行的杂交水稻研究的特殊案例中,人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四级网络固有的制度理想的积极影响,即专业技术人员与农民技术员的结合,以及农业研究团队与地方农业生产的结合。
首先,后来被广泛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以及袁团队另外两位创始成员李必湖和尹华奇(Huaqi Yin),都来自湖南省一个偏远农村乡镇的职业高中——安江农校(Anjiang Agricultural School)(谢长江(Xie Changjiang)1990,第65页)。该团队能够在1967年获得国家科委和湖南省科委的重大政治和后勤支持,是因为当时的政府政策和社会氛围鼓励利用基层人力资源,而不论其专业职称如何。没有这种特殊支持,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将会夭折。袁隆平作为一名农村职业高中的普通教师,在中国科学院主办的顶级期刊《科学通报》(Kexue tongbao)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随后受到了国家科委领导的特别关注。34如果不是当时盛行的亲基层、反精英主义的政策和氛围,这两件事都是不可想象的,这与四级网络所倡导的将农民人才融入农业科研的精神是一致的,尽管当时这个网络尚未正式建立。
其次,1970年,当袁隆平在安江农校经过六年艰苦工作后,其杂交水稻研究工作遇到巨大困难,几乎停滞不前时,他得到了时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要领导人华国锋(Hua Guofeng)的大力支持,华国锋鼓励袁隆平将研究工作与农民群众相结合,以推进杂交水稻研究。华国锋告诉袁隆平,农业科学进步离不开与农民和农田的联系。在这种特殊的鼓励和支持下——这与同样是四级网络背后的“群众路线”是一致的——袁隆平下定决心更加努力地继续他的工作。35
第三,袁隆平团队杂交水稻研究工作中最重大的突破,得益于1970年底海南省一位当地农民技术员的帮助。当时,袁隆平的团队正在海南省一个农场进行田野调查。在该农场工作的一位名叫冯克珊(Keshan Feng)的当地农民技术员,知道在附近何处以及何时可以找到野生稻品种,并在恰当的时间将袁隆平的助手李必湖带到了那个地点。他们共同鉴定出一种后来被称为“野败”的野生稻株,事实证明这是对三系法杂交水稻技术成功至关重要的雄性不育系。³⁶
上文已经揭示,中国杂交水稻技术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四级网络及其背后的“群众路线”精神,而MCE制度是其坚实的经济基础。1973年杂交水稻种子成功发明并于1976年开始广泛种植后,MCE和四级网络也在帮助农村集体控制杂交水稻种子生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自1958年以来,官方的种子生产政策是“四自一辅”,即农村集体应依靠自身进行种子的生产、选育、留存和使用,并辅之以必要的外部调拨(吴献之(Wu Xianzhi)1984,第32页;赵玉桥(Zhao Yuqiao)1998,第14-5页)。然而,由于技术能力有限,某些集体发现难以实施这一政策。华容县就是一个例子,该县在1969年之前严重依赖外部调拨种子。这种情况随着1969年四级网络的建立而改变,该网络使华容县能够在1970年生产出足够的种子供自身使用(湖南农业志编纂委员会 1985,第171页)。
当将“四自一辅”政策应用于杂交水稻种子时,四级网络在改善结果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初在1976年,典型的做法是鼓励各生产队自行生产种子。意识到这种做法存在许多与缺乏规模经济相关的缺点,县级或地区级政府决策者决定将杂交种子生产集中在远高于生产队的级别。湖南省再次提供了很好的例子。在零陵地区(Lingling Prefecture),一些地区选择将杂交种子生产集中在县级,而另一些地区则根据不同的地方条件将其确定在区级或公社级。结果比1976年更具生产力:面积、质量和数量都显著提高。在东安县(Dong’an County),情况类似,但这里的杂交种子生产从1977年开始以公社级农业科学站为中心,在那里,应被用来服务于农业科学研究和应用的三个关键要素——专业技术人员、农民技术员和普通农民——都得到了动员。有35名专业技术人员在公社农业学校培训了约1000名农民技术员,这些技术员反过来又与2000多名选定的普通农民(通常是贫下中农阶级出身)在专门的田块上生产杂交水稻种子。结果也比1976年有了显著改善。37
上述讨论表明,MCE提供了一个有利于四级农业科研网络的制度环境,该网络在推动杂交水稻技术进步以及通过打破专业技术人员与农民技术员之间、技术人员与农民群众之间的壁垒来促进杂交水稻种子的地方生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上,MCE下杂交水稻技术及其应用的成就不仅在毛泽东时代国家制作的材料中得到颂扬,而且也在西方观察家的著作中得到体现。例如,托马斯·B·温斯(Thomas B. Wiens)在反思中国在MCE下杂交水稻领域取得的成就时评论道:“通过建立‘四级科研网’(级别分别为县、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中国已经形成了一套能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同时实现稳定、地方适应性选择、评估和种子繁殖的体系。”(温斯 1978,第680页)
然而,随着去集体化,MCE解体了。随之而去的是四级网络。杂交种子的生产不能再依赖农村集体,因为后者已经消失了。个体农户在资金和技术上也无力承担这项任务。结果,中国的种子政策最终从“四自一辅”转变为“种子商业化”,授权专业的私营公司从事杂交水稻种子的生产和贸易(中国种子协会 2007,第28-35页)。为了适应新的制度环境,1999年成立了一家以袁隆平命名的股份公司,袁隆平拥有5%的股份。该公司于2000年以“隆平高科(Longping Gaoke)”的名称公开上市(齐淑英(Qi Shuying)和魏晓文(Wei Xiaowen)2002,第361-3页)。根据2012年10月的一份投资报告,隆平高科在中国杂交水稻种子市场的份额为20%,稳居第一位,2010年和2011年的净利润增长率分别为54%和79%(光大证券(Guangda Zhengquan)2012,第1页)。
随着地方集体对种子生产的控制被可能对农民行使寡头垄断权力的商业化种子公司所取代,人们有理由推测中国农民的贸易条件将会恶化。对此无法提供系统的数据,但最近发生的一件公共事件可能提供一些有用的参考。在一封致袁隆平的公开信中,一位最受尊敬的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评论说,在20世纪80年代,0.5公斤杂交种子只需1.5公斤大米即可购买,但如今购买0.5公斤杂交种子需要支付10公斤大米。如果贸易条件恶化,那么这将意味着种植杂交水稻的农民增加了额外的成本,因为他们必须在每个种植季节购买杂交种子。(李昌平 2011)
理论上,杂交水稻的价格可以由政府调控。然而,由于中国各地情况不同,中央政府并没有统一的价格管制政策。杂交种子价格的控制基本上由各省自行决定。
笔者仅能找到一个省级政府,即四川省,明确规定了杂交水稻种子的价格上限(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1)。根据各种新闻来源的估计,政府规定的价格上限仅略低于平均市场价格。38此外,规定是一回事,执行是另一回事。在腐败普遍存在的背景下,四川省这项政府法规的执行效果如何,尚难预料。

表2.6显示,随着从MCE向HRS的过渡以及HRS制度下时间的推移,中国杂交水稻播种面积占水稻总播种面积的百分比增长率呈现下降趋势。
在剔除最初两年,即1976年和1977年(由于其基数百分比极低,分别为0.38%和6%)的计算后,我们可以看到增长率从1978-1987年(这一时期的大部分年份可以说属于MCE时期,因为人民公社从1985年开始正式不再存在)的12.57%下降到1987-2002年(HRS时期)的2.98%。在HRS时期的1987-2002年内,增长率也呈现下降趋势:从1987-1991年的9.94%下降到1991-2002年的0.55%。当然,不应期望1991-2002年的增长率能保持与1987-1991年相同的速度,因为杂交水稻播种面积的份额增长存在自然限制。但1991-2002年这11年间从53.39%增加到56.73%的总增幅仍不能算作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
当我们考察另一个指标,即年均百分点增长时,同样的下降趋势依然存在,也就是说,1978-1987年期间的增长仍然大于随后的1987-2002年期间,而在1987-2002年第二个时期内,1987-1991年子时期的增长仍然大于随后的1991-2002年子时期。唯一不同的结果是,1987-1991年子时期的增长大于1978-1987年第一个时期。
考察后MCE时代杂交水稻播种面积指标下降的原因,将是超出本博士论文范围的另一项任务。这里的要点是,表2.6中的数据至少为基于先前定性讨论的论点提供了一些支持,即MCE在促进杂交水稻技术应用于中国农业生产方面表现良好。
杂交水稻的案例表明了一个重要观点:MCE很可能促进了绿色革命的某些重要遗产,例如杂交水稻技术,这些遗产被传承到HRS时代以供进一步发展和利用。然而,在继承MCE的这些遗产时,HRS的新制度可能导致了一些负面影响,例如放弃了对杂交水稻种子的地方控制。关于中国农民在杂交水稻种子方面的贸易条件是否恶化的问题,在此无法得出结论性讨论,尽管像李昌平信中提出的轶事证据表明情况确实如此。贸易条件问题将在下一节中更详细地讨论。
总之,去集体化通过三种方式影响了中国的农业生产。它对全国范围内的规模经济造成了损害,改善了约25%至30%村庄的劳动激励,并作用于但也逐渐贬低了从MCE时代遗留下来的遗产。总的来说,也就是说,综合考虑去集体化对中国农村农业生产产生的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影响,可以合理地说,去集体化对生产领域的净效应是负面的。
2.3 交换与分配领域
作为中国农村经济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去集体化的影响并不仅限于生产领域。农村经济活动的另外两个关键领域,即交换和分配,也受到了深刻影响。
2.3.1 交换领域
交换领域的主要指标是农村居民的贸易条件。其中涉及两个贸易条件因素。第一个是农产品与非农消费品和服务交换的条件。第二个是农产品与作为农业生产资料(或农业投入品)的工业产品交换的条件。
理论上讲,去集体化应该会对农村居民的贸易条件产生恶化影响。在集体解散为许多个体农户之后,大多数这些农户将不再控制生产非农消费品和农业投入品的地方农村企业(因为这些企业实际上已经私有化),更不用说地方农村地区以外或中国城市的企业了。面对这些以利润为导向、根据市场条件和利润最大化做出定价决策的企业,个体农户将成为市场力量薄弱的市场参与者。农村集体的解体也导致了公共服务(特别是教育和医疗)供给的商业化,因为学校、药店和医院现在也转变为受利润驱动的自主市场参与者。可以预见,农民的贸易条件将会恶化。
全国范围的经验证据似乎证实了这一点。在MCE下,工业品价格与农产品价格之比以及农业投入品价格与农产品价格之比持续下降,而在HRS下,这两个指标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上升趋势。
让我们首先看一下MCE下的贸易条件。本尼迪克特·斯塔维斯(Benedict Stavis)记录道,如果将1952年各种农村价格指数都设定为100,那么工业消费品价格指数与农产品价格指数之比从1952年的100%持续下降到1973年的57%,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与农产品价格指数之比下降更为显著,从1952年的100%下降到1973年仅约31%(斯塔维斯 1978,第260页,表10.1 农村价格指数)。这一证据表明,在MCE下,农民的贸易条件显著改善。
尼古拉斯·拉迪做了一项类似的研究,但他将工业消费品价格指数和农业投入品价格指数合并为一个价格指数,称为“农民购买的制成品价格指数”。同样以1952年的价格指数为100,他表明农产品价格指数与制成品价格指数之比持续上升,从1952年的100%增加到1981年的233.8%(拉迪 1983,第108页,表3.4 农业贸易条件,1952-81年)。拉迪的研究表明,在MCE下,农民的贸易条件显著改善。
20世纪90年代中期私有化进程开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从表2.7可以看出,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及以后(这是工业企业私有化加速的时期),总体趋势是农民贸易条件的恶化。向HRS的转变并没有立即与贸易条件的恶化联系起来,但去集体化和HRS在农村的引入(作为农村经济活动市场化)为随后的非农业企业私有化准备了条件,并且是其先兆。一个合理的解释可能是,一旦这些企业私有化并完全转向追求最大利润,它们就利用其垄断地位来提高农民支付的价格。HRS制度,加上向农民销售产品的企业的私有化,导致了农民贸易条件的恶化。
值得注意的是,出于对政治稳定的担忧,中国政府的价格指数通常不准确且存在显著偏差。如果考虑到这一点,表2.7仍然显示农民贸易条件恶化的趋势,尽管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显著,那么有理由相信农民的实际贸易条件可能确实比官方数据显示的恶化得更为严重。
除了全国范围的定量数据外,现有文献中也有一些著作详细记录了各省和地方农民贸易条件的恶化情况,特别是关于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和工业投入品价格上涨的情况(例如,参见梅1999,第27-30页)。

2.3.2 分配领域
除了以家庭为基础的(或自营的)农业生产和贸易外,后MCE时代的普通中国农村居民也参与了雇佣他们作为非所有者雇员的企业的生产活动。其中一些企业过去由当地农村居民集体所有,并由公社和大队管理部门经营,但去集体化通过市场化和私有化这些企业改变了这种关系。由于普通农村工人从这些企业获得的收入是由这些企业的所有者或管理者分配给他们的,因此它们属于分配领域。
理论上讲,去集体化对普通农村居民作为非所有者雇员参与的经营活动的分配结果具有两种类型的重大影响。
首先,正如本章开头所解释的,去集体化不仅是将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农业生产资料承包给个体农户,而且也是将现有的非农业公社和大队企业市场化(并最终从1994年起导致私有化)(去集体化后,从1984年起,它们被称为乡镇企业,或TVEs),并允许在中国农村建立新的私营企业。在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就业的普通农村居民的比例持续下降。私有企业主在指导乡镇企业经营活动方面权力日益增强的事实意味着利润成为优先事项,这不利于已成为非所有者雇员或向私营老板出卖劳动力的纯粹工薪阶层的普通农村居民的报酬条件。
其次,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HRS)总体上对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业活动产生了负面影响,这迫使大量自营农业劳动者进入中国城乡的资本主义部门,从而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产业后备军,特别是以日益增长的流动人口的形式出现,这进一步削弱了农村工人在农村乡镇企业和城市企业中相对于其老板的议价能力,并对其工资待遇施加了下行压力。

表2.8显示了1978年至2004年乡镇企业利润和劳动报酬的趋势。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在集体所有制企业工作的乡镇企业雇员占所有乡镇企业雇员的比例持续下降。但这并没有导致净利润与劳动报酬之比出现明确的趋势。利润-劳动比率最初呈现下降趋势,直到1990年。1990年之后,该比率持续上升。1990年前后这种对比的原因可能是什么?
毫无疑问,去集体化对中国农村产权的影响一直是持续减少集体所有制企业的份额,这主要是由于20世纪80年代及以后新兴私营企业的增加,以及从90年代中期开始现有集体乡镇企业的私有化。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去集体化也改变了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管理方式。
这种以市场化为名的变革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最初到1990年,集体乡镇企业的市场化采取了扩大集体乡镇企业自主权、摆脱乡镇行政直接控制的形式,并特别指导应提高劳动报酬水平。这项新政策与MCE时代形成鲜明对比,在MCE时代,公社和大队行政部门直接控制农村企业的经营活动,并为了促进中国农村经济的长期发展而刻意压低劳动报酬水平(或短期消费)。这项市场化集体乡镇企业的新政策导致了劳动报酬总体水平的提高以及管理者与工人之间报酬差异的扩大。从1990年开始,集体乡镇企业的市场化进一步深化,这次采取了事实上的私有化形式,即将集体乡镇企业承包给私人。值得注意的是,在市场化的第一阶段,承包制改革已经实施,但只是在局部地区,并且伴随着一些反复的抵制和摇摆。而这一次,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将集体乡镇企业承包给私人老板的做法在全国范围内持续推行。(张翼(Zhang Yi)和张松松(Zhang Songsong)2001,第79-83页;于力(Yu Li)等人 2003,第32-3页)
因此,在市场化的第一阶段(至1990年),即企业自主权扩大阶段,集体乡镇企业收入分配中的利润-劳动比率有所下降。新兴的私营乡镇企业为了与集体乡镇企业竞争人力资源,也提高了这一比率。根据这一阶段进行的一项调查报告,1979-1985年间,乡镇企业工资年均增长率为12.22%,超过了乡镇企业产值的年均增长率(10.75%)(劳动人事部 1989,第7页)。在市场化的第二阶段(1990年以后),即事实上的私有化阶段,先前利润-劳动比率下降的趋势发生了逆转,利润-劳动比率开始上升。毫不奇怪,在市场化的第二阶段让位于乡镇企业改革的新阶段,即从1994年开始的乡镇企业(法律上的)私有化之后,这一新趋势仍将持续(王(Wang)等人 1996,第689-98页)。
除了劳动报酬在乡镇企业净收入中所占份额下降外,农民工在中国城市也面临着不利条件。

从表2.9可以清楚地看出,自去集体化以来,外出务工的流动人口数量呈指数级增长。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流动人口数量的绝对增长尤其显著。如果流动人口的流量大于对其劳动力的需求增长,这将对农民工的工作和报酬条件造成下行压力。
正如劳动报酬与净利润之比在乡镇企业中一直在下降一样,农民工劳动报酬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也从1989年的16%下降到2003年的12%(中国国务院 2006,第12页)。
不仅农民工的工资相对于中国国民收入一直在下降,而且农民工实际工资的绝对水平很可能也在下降。一份被广泛引用的报告显示,珠江三角洲(Zhujiang River Delta)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在1992-2004年的12年间仅增加了68元,在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这代表着实际工资的下降(孙兆凡(Sun Chaofan)等人 2005;戴尔·温 2005,第23页)。当被问及2001-2006年期间对工资水平的感受时,中国东南部沿海经济发达省份浙江省(Zhejiang Province)25.6%的农民工表示工资没有增加,9.4%表示工资有所下降。中国东北部吉林省的相关百分比更为惊人:分别为36.3%和21.2%(邵奋(Shao Fen)2008,第127-8页)。
近年来,主流报道声称农民工工资大幅上涨。然而,更详细的调查显示,实际情况远比这复杂。在考虑通货膨胀以及血汗工厂为剥削工人而采取的各种措施(如无偿加班、更严格的扣款和罚款、拖欠工资和赖账、将福利待遇并入名义工资等)之后,农民工的实际工资很可能一直停滞不前。例如,为应对2010年一系列工人自杀事件以及随后公众的谴责,苹果(Apple)和其他西方主要品牌的代工巨头富士康(Foxconn)宣布为其深圳(Shenzhen)市的工人多次提高基本月薪,从2010年初的900元提高到2010年底的2000元。然而,独立调查显示,对于深圳的大多数富士康工人来说,即使到2012年1月,名义工资水平也仅为1550元,仅略高于深圳市政府规定的最低月薪1500元。另一方面,无偿加班现象更加频繁。一名工人在2011年10月加班86小时,但只计算了60小时。此外,在2010年6月之前,富士康工人的食宿是免费的,但在工资“上涨”后,这些费用将从工人的月薪中扣除。这意味着每月工资将额外扣除约400元。(富士康调查组 2012,第5节)
总之,去集体化对中国普通农村居民经济活动的生产、交换和分配领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在生产领域,影响非常复杂。虽然发生了显著的规模经济损失,但约三分之一的农村地区的劳动积极性可能确实有所提高。就MCE时代发展并传承给HRS时代的遗产而言,特别是“绿色革命”的成果(或现代工业投入品在农业中的可获得性),HRS很好地利用了它们,但同时也可能由于前面提到的规模经济的显著损失,限制了这些遗产潜力的进一步发展。
在交换领域,当普通农村居民用农产品交换现代农业生产资料和非农消费资料时,去集体化恶化了他们的贸易条件。与MCE时代相比尤其如此,在MCE时代,农业的贸易条件正在改善。
在分配领域,去集体化对普通农村工人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随着劳动报酬份额的下降,企业收入的分配越来越倾向于雇主,而牺牲了农村工人的利益。
2.4 对收入与支出的影响
就本章而言,从去集体化到农村贫困状况的因果链中有两个关键环节。
第一个因果联系是关于去集体化如何影响普通农村居民参与的经济活动。本章重点关注去集体化产生影响的三个经济活动领域,即生产、交换和分配领域。
第二个因果联系是关于这些影响如何作用于农村贫困的两个参数,即收入和必要支出(将收入与必要支出阈值进行比较可以得出贫困程度)。根据定义,贫困状况由收入水平和必要支出水平的相对关系决定。收入水平相对于必要支出阈值的提高将导致贫困减少。这方面最明确的情况是收入增加同时必要支出降低。其他情况,如必要支出增加但收入增加更多,或收入降低但必要支出降低更多,也会导致贫困减少。另一方面,收入水平相对于必要支出阈值的降低将导致贫困增加。这方面最明确的情况是收入降低同时必要支出增加。其他情况,如必要支出降低但收入降低更多,或收入增加但必要支出增加更多,也会导致贫困增加。
让我们看一下去集体化对收入水平的影响。去集体化,特别是与其后果——私有化相结合时,产生了以下影响。首先,对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生产领域)。其次,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相对于农产品价格上涨,导致贸易条件恶化(或不那么有利)(交换领域)。第三,普通农村工人的工资报酬在企业收入中所占份额下降(分配领域)。这些发展对普通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不利。
接着,让我们看一下去集体化对必要支出水平的影响。这比收入水平的情况简单,因为只有一个经济活动领域(交换领域)在这里起着关键作用。农村消费资料价格相对于农产品价格上涨导致的贸易条件恶化(或不那么有利),意味着去集体化对普通农村居民的必要支出水平产生了提高的影响。
总之,与传统观点相反,1978年后中国普通农村居民必要支出门槛的提高,加上一些对农村收入不利的发展,意味着农村贫困在此期间是否有所减少尚不确定。这为下一章对农村贫困趋势证据的仔细考察提供了理由。
第三章 重新评估1978年后农村减贫的成效
本章批判性地评估了中国1978年后农村减贫的表现,并讨论了农业去集体化(decollectivization)对这一表现所做的贡献。本章分为四个部分。首先描述官方统计数据所反映的1978年后中国农村贫困状况,并说明这些统计数据是如何产生的,即中国国家统计局(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NBS)自1978年以来衡量农村贫困所使用的方法和程序。然后在第二部分讨论官方统计数据时间不一致性偏差的主要来源,以及它们如何极大地夸大了1978年后中国农村减贫的成效。在第三部分,作者试图提出一套关于1978年后中国农村贫困的替代估算,以纠正官方统计数据中的这种偏差。第四部分讨论了农业去集体化在影响中国1978年后农村减贫成效方面的作用。
3.1 官方统计数据
3.1.1 1978年以来农村减贫的官方记录
关于中国农村贫困自1978年以来已大幅减少的普遍看法,是基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制定并发布的官方统计数据。³⁹根据这套统计数据,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从1978年的2.5亿急剧减少到2007年的1479万。同期,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从31.6%下降到2.0%(见下文表3.1)。从官方统计数据来看,中国在减少农村贫困方面无疑取得了惊人的成功。

3.1.2 官方贫困统计的方法
在我们着手评估这套官方统计数据的准确性之前,让我们首先了解中国国家统计局得出这些数据的程序。自1978年以来,国家统计局不间断地进行了年度农村住户调查(Rural Household Surveys, RHS),这为国家统计局估算中国农村贫困状况提供了原始的经验基础。然而,国家统计局并未基于年度农村住户调查结果,系统地逐年衡量1978年以来的中国农村贫困状况。相反,在1978-2007年期间,国家统计局仅对1984年和1998年进行了两次系统的农村贫困衡量,而对于所有其他年份,它通过将某个价格指数(可能是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即农村CPI)应用于基准年份的农村贫困线来简化估算.40
3.1.2.1 1984年的方法
1985年,国家统计局首次系统地基于1984年农村住户调查结果,对1984年的中国农村贫困状况进行了衡量。值得注意的是,国家统计局贫困统计数据所依据的贫困概念是绝对贫困(而非相对贫困),即满足日常生活基本需求所需的最低支出,国家统计局用以描述中国农村贫困状况的指标是贫困发生率,即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41具体的衡量程序分为三个步骤。前两个步骤的目的是计算农村(绝对)贫困线,第三个步骤的目的是通过将这条贫困线应用于农村住户收入分层数据来确定农村贫困的发生率。
农村贫困线包含两个组成部分:食物和非食物。第一步,通过将食物篮中不同种类食物的实物数量分别乘以其价格并加总结果,计算出农村贫困线的食物部分(也称为食物贫困线),即最低必需食物支出。食物篮中食物项目的数量是根据每日最低2400千卡(由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热量摄入水平以及每日热量摄入低于2400千卡的农村居民的实际消费模式确定的。第二步,农村贫困线的非食物部分(也称为非食物贫困线)随后被计算为食物部分的固定百分比(三分之二)。农村贫困线的这种非食物与食物部分的比例意味着总消费支出的60%用于食物。这大致等于当时中国农村家庭平均食物支出份额(也称为恩格尔系数(Engel's coefficient))(帕克(Park)与王(Wang),第387页)。
前两个步骤完成后,1984年的农村贫困线计算为200元。第三步,使用农村住户收入数据对照这条贫困线,以确定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数量。那些人均收入低于200元的农村居民在1984年被视为生活在贫困之中。因此,1984年的农村贫困人口估计为1.28亿。然后可以通过将农村贫困人口除以农村总人口来计算农村贫困发生率(15.9%)。
1985-1997年各年份的官方统计数据是通过对1984年农村贫困线按照这些年份的某个价格指数进行调整而得出的。1978年的统计数据制作方式略有不同:第一步,采用了与1984年相同的食物篮,但所使用的这些食物项目的价格是1978年的价格(唐(Tang)1994年,第41页)。1990年也值得一提。由于计算农村家庭收入时用于评估自产自销产品的价格在1990年从计划价格变为加权收购价格(反映了市场化改革),食物贫困线的计算也相应调整,导致1990年农村贫困线大幅提高(唐1994年,第41页;帕克与王,第387页)。
3.1.2.2 1998年的方法
1998年,当国家统计局第二次系统地衡量1998年中国农村贫困状况时,引入了三项重大变化。
首先,在计算食物贫困线的步骤中,每日热量摄入标准从2400千卡/天降至2100千卡/天,消费模式从每日热量摄入低于2400千卡的人群的消费模式变为收入低于800元人群的消费模式。
其次,在计算非食物贫困线的步骤中,国家统计局采用了一种由世界银行(World Bank)专家马丁·拉瓦利(Martin Ravallion)发明的全新方法论,取代了1984年首次采用并一直沿用至1997年的恩格尔系数方法论。拉瓦利基于给定的食物贫困线,开发了一种独特的方法来计算非食物贫困线(拉瓦利он1994年,第118-26页)。最终结果是两条不同的非食物贫困线(一条较低,一条较高)。较低的线等于人均消费水平与食物贫困线持平的家庭的人均非食物支出。较高的线等于人均食物消费水平与食物贫困线持平的家庭的人均非食物支出。在这两条非食物贫困线之间,国家统计局采用了较低的一条。在1998年做出这一改变后,非食物部分在农村贫困线中的份额从40%降至仅17%。
第三个重大变化发生在根据农村贫困线估算农村贫困人口数量的步骤中。与1984年仅使用人均收入来确定谁生活在贫困中的做法不同,1998年国家统计局开始采用双重标准,即同时使用收入和支出数据来确定农村贫困状况。具体来说,如果家庭人均收入低于贫困线且人均消费低于贫困线的1.5倍,或者如果消费低于贫困线且收入低于贫困线的1.5倍,则该家庭被认为是贫困的(帕克与王,第388页和第390页)。
对于1998年之后直至2007年的年份,国家统计局通过对1998年的贫困线按照这些年份的某个价格指数进行调整来计算其农村贫困线。
3.2 官方统计数据的时间不一致性偏差
3.2.1 对官方统计数据的批评
就其推理性质而言,现有对中国官方农村贫困统计数据的批评可分为两种分析上截然不同的类型。不过,这两种类型在逻辑上并不相互冲突:同一位研究者可以同时持有这两种类型的批评。
第一类批评侧重于官方农村贫困线的绝对水平,认为其过低。贫困研究领域的独立研究人员以及致力于减贫的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都属于这类批评的支持者。中国国家统计局对此做出了回应,于2008年将农村贫困线提高至1196元,较2007年的785元有大幅提高,同时宣称这反映了一个新的、更高的贫困标准。对照这条农村贫困线,2008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大幅增加至4007万人,同样较上一年(2007年为1479万人)大幅增加。然而,仍有大量批评认为,即使是这条新提高的贫困线,也仍然低于国际标准。关于这类批评的一个有趣事实是,尽管对于中国官方统计数据中报告的农村贫困线和农村贫困人口水平过低存在广泛争议,但所有批评者都出人意料地同意官方统计数据的结论,即1978年后时期农村贫困已大幅减少。例如,世界银行最近的一项研究(陈(Chen)和拉瓦利2008年)明确得出结论,尽管今天中国应采用更高的农村贫困线,这将显示出更大数量的农村居民仍生活在贫困中,但当把同样更高的贫困标准应用于1980年代初的年份时,农村贫困人口的数量也会大幅增加,而中国在经济改革时期农村减贫的记录将更加令人印象深刻。这一论点既有价值,也有缺陷。其价值在于指出了制定一个随时间推移反映一致贫困标准的重要性。其缺陷在于,它与国家统计局的官方统计数据一样,存在相同的时间不一致性偏差,因为它依赖于一个有偏的官方价格指数来调整非基准年份的贫困线。
这就引出了第二类批评,它关注的是农村贫困标准在时间上是否一致。对于这类批评而言,农村贫困线和人口的绝对水平是高是低并非问题所在;重要的是同一贫困标准是否在时间上得到一致应用。因此,它试图找出官方农村贫困统计数据中时间一致性的偏差。然而,尽管如此,这类批评中的大多数令人惊讶地停留在指出时间不一致性偏差的某些来源的层面上,而没有进一步努力评估这种偏差对中国1978年后时期农村贫困线或农村减贫成效的总体影响程度.42
在本节的下一部分,作者将沿着第二类批评的思路进行努力。作者将找出1978年后中国农村贫困官方统计数据中时间一致性偏差的主要来源,并简要分析它们如何都对农村贫困线或农村贫困人口产生向下的影响。
3.2.2 官方统计数据时间不一致性偏差的来源
为了准确评估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内的减贫成效,必须在整个贫困估算过程中采用相同的贫困标准。然而,已有充分文献证明,国家统计局在衡量1978年后中国农村贫困的方式上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改变了隐含的贫困标准(帕克与王 2001年;罗斯金(Riskin)2006年;拉瓦利与陈 2007年;张全红(Zhang Quanhong)2010年)。其中一些问题对结果的影响是模糊的或微不足道的。对这一问题的仔细研究发现,官方农村贫困估算存在六个主要问题,这些问题对结果产生了明显的、明确方向的偏向性影响,有趣的是,它们都指向同一个方向——随着时间的推移,低估了农村贫困。总的来看,官方统计数据时间不一致性偏差的这六个来源显然产生了一种低估农村贫困发生率和夸大1978年后中国农村减贫成效的效果。
3.2.2.1 食物贫困线的下降
第一个问题是1998年引入的食物贫困线下降,原因是最低每日热量摄入水平从2400千卡/天降至2100千卡/天,以及消费模式从每日摄入低于2400千卡人群的消费模式变为收入低于800元人群的消费模式.43不言而喻,降低热量摄入标准会使食物贫困线向下偏离。消费模式变化的影响更为模糊,但很可能它也具有使食物贫困线向下偏离的效果,因为1984年每日摄入低于2400千卡人群的消费模式比1998年收入低于800元人群的消费模式涉及更昂贵的食物选择.44因此,在1998年引入新方法论具有使食物贫困线向下偏离的效果。
3.2.2.2 非食物贫困线与食物贫困线之比的下降
第二个问题是1998年引入的非食物贫困线与食物贫困线之比的下降。国家统计局采用马丁·拉瓦利的较低非食物贫困线,导致农村贫困线中非食物与食物部分的比例大幅下降,从1998年以前年份的40%:60%降至1997年以后年份的17%:83%。为了使这种大幅下降不导致时间不一致性偏差,食物价格的上涨速度必须远高于非食物价格,从而使名义非食物支出占食物支出的份额缩小。然而,对1984-2007年期间价格趋势的实证研究表明,情况并非如此。如下表3.2所示,1984年至2007年间食物价格的上涨并未超过非食物价格的上涨。相反,如果在2007年保持基准年份1984年消费各组成部分相对份额的实际标准,食物的相对份额将从1984年的59%下降到2007年的57.9%。换句话说,为了在时间上保持一致,非食物与食物贫困线之比在1984-2007年间应略有增加,而不是大幅减少。

值得澄清的是,尽管国家统计局编制的价格指数数据因其时间不一致性问题而广受批评(尤其参见下文第3.2.2.3节),但这个问题并不妨碍对食物份额和非食物份额随时间进行有意义的横向比较。然而,另一方面,鉴于表3.2所依据的数据并非仅针对农村贫困人口,也并非包含所有年份全部消费组成部分,因此在此仅作为参考点,即表明非食物与食物之比在1984-2007年间基本保持不变,而大幅降低该比例,如1998年国家统计局方法论所引入的那样,将严重使非食物贫困线向下偏离。因此,我不会基于表3.2计算2007年非食物与食物之比。相反,我认为保持最初用于1984年的40%:60%的比例更有意义。
3.2.2.3 不准确的价格指数
第三个偏差来源是使用不准确的价格指数来得出除基准年以外年份的农村贫困线。人们普遍认为,国家统计局使用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来计算非基准年份的农村贫困线。CPI的质量高度依赖于“篮子”中的商品和服务,因此,它极易受到人为操纵,以服务于掩盖实际收入停滞水平的政治需求。近来,中国国内已形成一种公众共识,即官方CPI高度不准确,至少应提高三倍才能忠实反映1978年后时期的通货膨胀现实(万小西(Wan Xiaoxi)2006年,郑建人(Zheng Jianren)2007年,以及徐一胜(Xu Yisheng)2009年).45更糟糕的是,国家统计局用于制定官方农村贫困统计数据的价格指数似乎甚至低于农村CPI(帕克与王,第389页)。这产生了一种累积效应,即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低估农村贫困线。
3.2.2.4 低估的健康和教育支出
第四个偏差来源是未能将商业化的公共服务(如教育和医疗保健)迅速增加的支出纳入农村贫困线。中国经济改革初期农村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以及随后的公共服务商业化,导致为日益昂贵的教育和医疗保健服务付费的财政负担从集体/政府大规模转移到个体家庭。例如,巨额的医疗费用是导致很大一部分人即使知道应该就医(2003年为50%)或住院(2003年为30%)也未能如愿的重要因素(世界银行2005a,第2页)。根据另一项独立研究,高昂的医疗和教育费用使相当一部分(1988年为1.6%,1995年为4.3%)农村居民陷入贫困(古斯塔夫森(Gustaffson)和李(Li)2004年,第296页)。然而,这一重大变化并未反映在官方农村贫困线的估算中(李和小强(Li and Zhu)2004年;古斯塔夫森和李2004年;世界银行2005a)。需要在基准年农村贫困线的构成中增加教育和医疗保健支出的权重,并且必须相应调整农村CPI,否则农村贫困线将被向下偏置。
3.2.2.5 农民工面临被低估的贫困线
第五个偏差来源是,对于那些在生活成本高得多的中国城市地区度过相当一部分时间的农民工而言,其贫困线被低估了。在农村住户调查中,农民工被视为农村居民(中国国家统计局 2007年,第369页),因此他们从城市工作中获得的收入被视为农村家庭收入的一部分,但他们的贫困状况仍然由农村贫困线决定,尽管他们的大部分支出是用于满足在中国城市背景下的基本消费需求。随着农民工数量从1990年代初开始呈上升趋势(1991年为233万人,占农村人口的0.3%,1994年增至7000万人,占农村人口的8.2%,并持续稳步增长至2007年的2.1亿人,占农村人口的28.9%;见陈2006年,第28-9页及本论文,第111、137页),这种官方农村贫困估算做法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地使农村贫困线向下偏离。
3.2.2.6 从单一标准(收入)转向双重标准(收入和消费)
第六个偏差来源是,在1998年用收入和消费的双重标准取代了1998年以前所有年份一直使用的单一收入标准,作为衡量农村居民贫困状况的农村贫困线的适用标准。
根据1998年的双重标准,农村贫困人口由两组家庭构成(两者之间存在重叠):(1) 人均收入低于贫困线且人均消费低于贫困线1.5倍的家庭,以及 (2) 消费低于贫困线且收入低于贫困线1.5倍的家庭。与1984年的收入标准相比,1998年的方法论进行了一项减法和一项加法:它减去了人均收入低于贫困线但消费高于贫困线1.5倍的家庭群体,并增加了人均收入在贫困线1.0至1.5倍之间但消费低于贫困线的家庭群体.46
如果我们假设收入与消费之间存在长期均衡,那么1998年方法论所排除的人口数量将大于其纳入的人口数量。这会产生低估农村贫困人口和高估农村减贫成效的净效应。
一项实证检验证实了这一逻辑推理:如果使用1984年的方法论(单一收入标准)来衡量2007年农村贫困发生率,即,如果我们将2007年官方农村贫困线785元应用于2007年农村住户收入分层数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08年,第63-6页),假设收入阶层内部分布均匀,那么我们会发现2007年农村贫困发生率为2.9%,这个数字高于国家统计局(中国国家统计局2009年,第57页)47遵循1998年收入与消费双重标准方法论发布的数据(1.6%)。
3.2.3 系统消除时间不一致性偏差的必要性
总而言之,上述中国官方农村贫困估算方法论中时间不一致性偏差的六个来源,应对官方农村贫困估算产生显著且累积的向下影响。如果不消除这种偏差或其对官方估算的影响,我们将无法准确评估中国在1978年后时期的农村减贫成效。
代表上述第二类批评的现有文献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并包含了一些零星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针对有限的时间段提出了替代性估算,并纠正了偏差的某些来源,但仍然缺乏系统、严谨的努力来为中国农村贫困提供一套替代性估算,以纠正整个1978年后时期所有已知的主要时间不一致性偏差来源。我们迫切需要这样的努力,作为正确评估中国1978年后农村减贫成效的基础。
由于未能实现这一点,第二类批评与上文提到的第一类批评产生了相同的净效应,即同意官方统计数据的结论,认为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时间不一致性偏差问题,中国在1978年后时期的农村减贫仍然取得了巨大成功。
3.3 替代性估算
由于上文讨论的中国官方农村贫困统计数据中的六个偏差都具有夸大1978年后中国农村减贫成效的作用,因此毫无疑问,中国农村减贫的实际记录应不如官方统计数据所显示的那么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官方统计数据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有多大仍有待检验。在本节中,我将尽可能系统和严谨地做出初步努力,为1978年后时期(更具体地说是1978-2007年)的中国农村贫困估算开发一套替代方案,该方案不受前述六个问题导致的时间不一致性偏差的影响。目的是获得对这一时期中国农村减贫成效的更准确估算。
这项任务的本质是在对1978年和2007年进行估算时,保持1984年贫困标准在时间上的一致性。由于1978年的官方估算没有已知的时间一致性偏差,剩下的任务是为2007年制定替代性估算。这包括五个步骤:(1)基于国家统计局为1984年采用的相同的每日2400千卡标准和相同的食物篮,计算2007年的替代性食物贫困线;(2)基于国家统计局为1984年采用的相同的非食物与食物之比(40%:60%),计算2007年的替代性非食物贫困线;48(3)计算第二步中替代性非食物贫困线尚未包含的农村人均健康和教育额外支出;(4)计算农民工因在中国城市生活成本增加而带来的农村人均额外消费支出;以及(5)检查2007年农村住户收入分层数据,以估算2007年农村贫困的发生率。
将前四个步骤的结果相加,我们将得到2007年中国农村贫困线,该贫困线不受上一节讨论的前五个时间不一致性偏差来源的影响。以这条农村贫困线为标准,在第五步中,我们便可以得到2007年农村贫困发生率,该发生率不受之前讨论的第六个偏差来源的影响。
3.3.1 食物贫困线
如前所述,本论文坚持采用1984年确立的相同食物消费标准,即国家统计局在计算1984年官方农村贫困线时采用的每日2400千卡标准和相同的食物篮。另一方面,在确定2007年食物价格水平时,不应使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村CPI或其他现成的综合指数)价格指数,因为它们存在公认的向下偏差。为了计算2007年的食物价格水平,我使用来自不同来源的原始数据编制了一套替代数据。我从2007年中国城市销售的食品价格数据开始(中国物价年鉴编辑部 2008年,第453-4页)。然后,为了将其转换为农村价格数据,我利用2004年发布的关于中国城乡销售食品价格水平的数据集(这些数据集仅适用于2004年)来计算农村与城市价格之比。假设该比例在2007年保持不变,通过将2007年城市食品价格乘以该比例,我们可以得到2007年农村食品价格。结果列于下表3.3。

在获得2007年城乡食品价格后,便可以利用国家统计局在确定1984年农村贫困食物贫困线时应用的食物篮构成信息,来计算2007年农村食物贫困线。值得再次强调的是,通过遵循1984年的食物篮,在计算2007年农村食物贫困线时保持了相同的每日2400千卡能量摄入标准和相同的消费模式。结果如下表3.4所示。从该表中,我们可以看到估算的2007年农村食物贫困线为1129.53元。

3.3.2 非食物贫困线
在第3.2.2.2节中已经论证过,为了在1978年后时期保持农村贫困标准的一致性,1984年非食物贫困线与食物贫困线之比,即40%:60%,也应适用于2007年。遵循这一简单原则,我们通过将食物贫困线1129.53元乘以40%:60%,便可以轻松得到2007年非食物农村贫困线。结果是753.02元。将食物和非食物贫困线相加,我们得到估算的2007年农村贫困线:1882.55元。
3.3.3 健康与教育支出调整
由于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已将先前由国家运营和补贴的医疗和教育部门市场化,1984年及更早时期同等数量的医疗保健和教育消费在2007年将花费更多资金。鉴于国家统计局的官方贫困统计数据并未充分包含这种制度变迁对农村居民医疗保健和教育支出的影响,我们必须将2007年官方农村贫困线遗漏的此类费用部分加回到其中。
3.3.3.1 健康
正如之前分析过的(见第3.2.2.4节),在1978年后的时期,中国的医疗保健费用大幅增加。这种现象不应被视为医疗保健质量大幅提高的结果,也不应归因于人们为追求超出必要的更高健康水平而增加医疗保健支出。首先,中国一些关键的健康绩效指标在1978年后时期有所恶化,这当然不能解释为医疗保健质量的整体提高(世界银行2005年;王绍光(Wang Shaoguang)2003年)。其次,至少就疾病而言,治疗疾病所产生的医疗费用应被视为维持基本健康的必要或最低费用。这些费用不同于例如用于膳食补充剂或健身房会员卡的医疗保健支出,后者是为了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健康。第三,只要不同类型的药物能够以同样有效的方式治疗特定疾病,其质量就不应存在差异。在中国,廉价的传统中医药和治疗方法已逐渐让位于更昂贵的西药和治疗方法,但仅仅因为西方产品和服务更昂贵,并不意味着它们的质量更好。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传统中医药在对抗疾病方面既可以更便宜也更有效。下文表3.5-3.8显示了2007年中国农村地区的人均住院和门诊费用。


由于住院和门诊治疗的需求(而非需要)取决于个人的健康状况,而不取决于其收入水平,因此将一个普通贫困人口的必要健康支出视为与社会平均水平相当是合理的。中国卫生部(Ministry of Health, MOH)每五年进行一次全国健康调查(National Health Survey, NHS),并报告一些对计算必要健康费用有用的关键指标结果。第一个指标是过去两周内就诊总次数与受访人数之比(“过去两周就诊频率”)。第二个指标是过去两周内生病但未就医的人口比例(“过去两周未就医率”)。
有了这两个指标的数值,我们就能了解普通人多久生病一次,从而计算出维持健康每年人均需要多少次就诊。然而,我们不应假设所有选择不就医的人都应该去看医生。有些人可能觉得自己的病不严重,可以通过人体的自然防御功能自愈。因此,全国健康调查提供的另一个指标,即因经济原因未就医的患病者百分比,就变得很重要。因非经济原因未就医的患病者(见表3.6)应从每年人均必要就诊次数的计算中排除。因此,计算每年人均必要就诊次数的公式变得复杂。首先,我们必须计算总的必要就诊次数(即不考虑因非经济原因未就医的人)。这是通过将“过去两周就诊频率”乘以26(周),然后除以(1-“过去两周未就医率”)来完成的。其次,这个总数必须乘以(1-“所有患病案例中非经济原因未就医的百分比”),以消除因非经济原因未就医人群的影响。最后,结合2007年每次门诊费用的数据(该数据可在《中国卫生部2008》中找到),就可以计算出2007年每人总的必要就诊费用。这是医疗费用调整的门诊部分。
同理,可以计算2007年医疗费用调整的住院部分。全国健康调查也提供了与上述指标类似的指标。三个指标很重要:年住院频率(住院费用情况下不是“2周”)、未住院率以及因经济原因未住院案例的百分比。按照与必要门诊费用相同的计算方法,我们可以计算出2007年每人总的必要住院费用。
从表3.5-3.8可知,估算的2007年中国农村居民必要健康支出为门诊费和住院费之和,即473.34+238.14=711.28元。当然,应该还有其他类别的健康支出,但由于数据可得性有限,我只能对门诊和住院费用进行可靠的估算。同样值得强调的是,实际上,由于农村卫生设施和服务标准总体上不尽如人意,农村居民常常不得不去城市医院进行门诊和住院治疗。以中国农村普遍的门诊和住院费用作为农村居民的成本,存在低估农村居民健康支出的倾向。因此,我们应将上述估算的农村居民必要健康支出,即2007年的711.28元,解释为一个相当保守的估计。2007年农村居民平均实际必要健康支出应高于此数。
在我们能够将这笔钱加到先前估算的2007年农村贫困线之前,我们必须从中减去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农村居民根据从2003年开始引入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可以获得的报销金额。尽管这个新制度运行得并不好(王烈军(Wang Liejun)2005年,第98-101页),但农村参与者在2005年有权获得3.42%的有效报销率(张林秀(Zhang Linxiu)等人 2005年,第50页).49从711.28元的必要健康支出中减去这部分报销,剩下686.95元。

需要减去的第二部分资金是已经包含在估算的2007年农村贫困线1882.55元中的医疗保健支出。按照表3.9计算的份额,应从1882.55元中扣除5.43%,即102.22元。从686.95元中减去这个数额,剩下584.67元。这584.67元应加到前两个步骤估算的2007年农村贫困线1882.55元中。50
3.3.3.2 教育
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也促进了教育支出的迅速增加。为回应社会对平等受教育机会的广泛要求,中国政府在2006-2007年免除了所有农村地区基础教育阶段(小学和初中)学生的学杂费。据估计,这项政策使一名初中生受益180元,一名小学生受益140元.51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农村学生不再需要在教育上花钱。教材、文具等仍需学生家庭自掏腰包购买。一个更为重要的教育费用来源是中国农村地区已持续实施多年的学校合并计划。结果,小学和中学的数量都在持续快速减少。这导致了一系列本可避免的费用类别,如交通、取暖以及食宿(杨桂萍(Yang Guiping)2009年)。目前尚无关于这些额外费用具体数额的全国性数据,但对河北省(Hebei Province)某乡镇的一项地方研究显示,小学生每年平均额外交通费用为441元,初中生每年为738元(陈国强(Chen Guoqiang)2008年,第2页)。
与学校合并计划相关的教材文具、食宿和取暖费用也相当可观。但由于没有依据来确定这些费用中超出普通农村贫困线已包含部分的数额,在本论文中,作者并未估算学校合并计划导致的这些类别的额外费用。然而,交通费用的情况有所不同。由于如果学校合并计划不存在,这类费用根本不会发生,因此产生的交通成本应被视为必须添加到现有普通农村贫困线中的新费用(其他支出类别,如文具、食宿和取暖则不同,因为即使没有学校合并计划,它们在不同程度上仍然存在)。
假设此引用的地方研究中的额外交通费用能够代表中国农村其他受学校合并计划影响的地区,我们可以估算出应在农村贫困线基础上增加多少额外成本。

从表3.10我们估计,中国农村有1108.2万名初中生和4119.2万名小学生受到学校合并的影响,并可能成为额外交通费用的受害者。假设其中一半确实承担了额外的交通费用,那么这些初中生和小学在2007年农村总人口中所占的份额分别为0.76%和2.83%。将这两个百分比分别乘以2008年初中生增加的交通费用707.57元(738元除以2008年农村交通价格指数104.3%,取自中国国家统计局2009b,表8-3)和小学增加的交通费用422.82元(441元除以104.3%),并将结果相加(5.61元和12.48元),我们可以得到2007年中国农村地区每人估算的额外教育费用:18.09元。
3.3.4 农民工调整
计算农民工给2007年农村贫困线带来的额外必要消费成本是相对简单的。根据《人民日报》(People’s Daily)的一篇新闻报道52,2007年农民工总数达到了2.1亿。由于通常情况下许多农民工在其家乡的乡镇范围内工作,我们必须将这些人从我们的计算中排除。然而,2007年没有这方面的数据。根据2009年的数据(农民工总数为2.2978亿,其中1.4533亿在中国城市地区工作53),我们可以假设2009年和2007年城市务工农民工与农村务工农民工的比例相同,从而计算出2007年在中国城市地区工作的农民工数量。结果是1.3282亿。
在计算农民工给2007年农村贫困线带来的额外成本时,本文仅考虑食品和医疗保健支出。其他类型的支出,例如农民工家乡与其城市工作地点之间的住房和交通费用,也很重要。然而,由于数据可得性有限,无法对它们进行准确估算。对于其他消费类别,如服装、家居用品和教育,可以合理假设没有太多额外成本,因为他们可以从中国农村地区带来这些产品。
为计算额外的食物成本,我们保持与计算农村食物贫困线时相同的每日2400千卡标准和相同的食物篮。从表3.4可知,2007年中国城市地区的必要食物支出为1289.81元,比中国农村地区的必要食物支出(1129.53元)高出160.28元。为计算额外的医疗费用,我们参考表3.5-3.8,并得出城市医疗费用高出农村医疗费用的确切金额。结果是,门诊费用额外增加337.71元(811.05-473.34),住院费用额外增加482.38元(720.52-238.14)。额外总金额为820.09元。考虑到农民工可能会选择返回中国农村地区接受治疗(但这样他们会产生额外的交通费用),并且理解到这可能会对计算结果产生向下的偏差,我们可以假设农民工在城市逗留期间,其医疗治疗在城乡之间各占一半。这将使其额外医疗费用减少到410.05元(820.09元/2)。
我们需要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农民工在中国城市逗留的时间。对此没有精确的数据。然而,我们可以做一个粗略的估计作为替代。由于只有在中国城市居住超过六个月的人才被纳入国家统计局的城市务工农民工数量中,我们可以取6个月和12个月的平均值,并假设平均而言,一个城市务工农民工在中国城市居住9个月。这意味着上述估算的额外食品和医疗费用的四分之三将对2007年的农民工有效。确切金额为(160.28 + 410.05)75%=427.75元。
最后的步骤是将这427.75元分摊到2007年全部农村人口中。公式是将427.75元乘以城市务工农民工占农村总人口的百分比。54确切金额为427.75(132.82/727.50) =78.09元。这是我们应加到2007年农村贫困线上的、由农民工带来的额外必要成本。

替代性2007年中国农村贫困线各组成部分的估算值列于表3.11。
3.3.5 应用收入分层数据
在估算出2007年的替代性农村贫困线(2563.40元)之后,我们的下一步是将2007年的农村住户收入分层数据应用于这条贫困线,以估算生活在这条修正后贫困线以下的农村居民所占的百分比。


表3.12显示,2007年收入低于2500元的农村居民百分比为31.747%。由于替代性的2007年农村贫困线2563.40元落入2500-3000元收入组内,我们必须假设该收入组内收入均匀分布,以便估算该收入组对2007年农村贫困发生率的贡献。
第一步是计算该收入组中收入低于2563.40元的人口比例。假设收入均匀分布,结果是12.68%(公式为[2563.40-2500]/ [3000-2500])。第二步是将此百分比乘以该收入组在农村总人口中所占的份额。结果是1.289% (12.68%*10.168%)。
将这1.289%加到2007年收入低于2500元的农村人口百分比(31.747%)上,我们得到2007年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33.036%。鉴于2007年中国农村人口数量为7.275亿,这一贫困发生率意味着2007年有2.4034亿人生活在贫困之中。
3.3.6 补充说明
由于2007年的替代性农村贫困线基于五个要素,因此了解这些要素的不同组合如何不同地影响1978年后农村减贫的成效将会有所帮助。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将整个替代性贫困线应用于收入分层数据,而只应用其中的某一部分,将会发生什么?
首先,让我们只应用“食物”和“非食物”要素,即假设替代性贫困线仅由这两个要素构成。这样,2007年的替代性贫困线将为1882.55元。使用与第3.3.5节相同的方法,农村贫困发生率将为18.828%,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将为1.3697亿。
其次,让我们在已经包含“食物”和“非食物”要素的替代性贫困线基础上,增加“农民工调整”和“教育调整”要素,也就是说,我们只将“健康调整”要素排除在替代性贫困线之外。这样,贫困线将变为1978.73元。当应用于2007年收入分层数据时,计算出的农村贫困发生率将为20.698%,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将为1.5058亿。
这两项演练表明,即使我们将某些重要因素从替代贫困线中剔除,估算出的农村贫困状况仍然非常严重。这里值得再次强调的是,2007年的替代性农村贫困线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保守的估计——它应被解释为2007年农村贫困线的底线或最小值,不应以任何方式打折扣。在演练中将“健康调整”因素剔除并不意味着它应该被排除在替代贫困线之外。相反,它应该被包含在替代贫困线中。这些演练的目的是表明,即使我们将一个必要且重要的部分(“健康调整”因素占整个替代贫困线的四分之一以上——22.81%)从替代贫困线中剔除,2007年的农村贫困状况仍然会非常严重。
再次强调将“健康调整”要素纳入替代贫困线的理由是值得的。
首先,健康是人类基本需求的一个基本要素,如果一个人因为无力负担某种医疗保健而无法维持健康,那么为了恢复健康而获得相关医疗保健所需的费用,必须计为该人满足生活基本需求的必要支出的一部分,即贫困线的一部分。
其次,作者对2007年农村贫困线的替代性估算中所包含的医疗费用类型,确实是维持健康所需的最低和必要医疗费用。仅计算了生病情况下的住院和门诊费用。这些费用与去健身房、参加健康讲座或购买膳食补充剂无关。它们关乎对抗疾病的基本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本论文采用的健康概念是一种消极的概念,即关于摆脱不健康状况,而不是主动寻求更好的健康或“投资”于长寿。毫无疑问,这种消极的健康概念应被视为贫困线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第三,这个“健康调整”要素是一个调整项,这意味着并非所有的门诊和住院费用都被整合到替代贫困线中。相反,它是超出旧贫困线已包含的医疗费用的那部分金额被整合到替代贫困线中——因此使用了“调整”一词。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意味着毛泽东时代末期的必要医疗费用已经包含在旧贫困线中。这些费用足以使农村居民保持健康。现有文献中没有报告称在毛泽东时代末期的集体经济体制下,农村居民因负担能力问题而无法获得医疗保健。相反,现有文献中关于毛泽东时代农村医疗保健体系的著述都称赞其全面、可负担且普及。在此列举一些证据是很重要的。
在1984年为世界银行出版的一份刊物中,帕金斯(Perkins)和优素福(Yusuf)详细记录了毛泽东时代末期中国农村居民平均每人每年的医疗费用。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费用为每年7.5元。每次到大队卫生所就诊需支付0.05至0.1元的挂号费,病人只需支付少量药费。即使是那些被转诊到县医院进行大手术的人,由于总费用低廉且有50%的报销率,病人自付的费用大约为每次大手术10元,这在广大农村居民的承受范围之内(帕金斯和优素福1984年,第141页)。
基于这份文献,我们可以做一个有趣且有用的推演。从表3.5我们知道,2007年农村居民必要的就诊次数为4.60次。从表3.6我们知道,2007年农村居民需要的住院服务频率为0.076次。假设毛泽东时代末期的农村居民也需要相同数量的住院和门诊服务,那么我们就可以对1978年农村居民的人均医疗费用做出合理的估计。让我们取挂号费的较高值,即每次就诊0.1元。乘以4.60,即为0.46元。假设少量药费与挂号费相同,即0.1元,那么每人每年的总门诊费用将为0.92元。在住院费用方面,我们可以将大手术的费用作为住院费用的代表,即每次住院10元,乘以频率值0.076后,即为每人每年0.76元。因此,加上人均保险费用2.5元、门诊费用0.92元和住院费用0.76元,1978年农村居民每人每年的总必要医疗费用将为4.18元。
这个估算数额与我们从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中可以得到的数据相符。在《中国国家统计局1985a》(第198页)中,列出了1978年中国农村居民平均的各类消费支出。总消费支出为116.08元,与当年的农村贫困线100元水平相当。细目如下(单位均为元):食品78.59,衣着14.74,燃料8.28,住房3.67,日用品及其他7.62,文化生活服务3.16。“日用品及其他”和“文化生活服务”具体指什么尚不清楚,但两者都可能与医疗费用有关(当然它们也应包括教育和旅行等其他商品和服务的费用)。将这两个组成部分加在一起,总额为10.78元。先前估算的医疗费用4.18元,似乎与这个总额非常吻合,因为4.18元肯定远小于10.78元,并且似乎占后者的一个合理百分比。因此,可以说1978年的农村贫困线已经包括了农村居民的必要医疗费用。这就是为什么“健康调整”要素必须纳入2007年农村贫困线的替代性估算中。1978年中国农村居民有权获得的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已由1978年的农村贫困线所覆盖,应继续纳入2007年的农村贫困线,并且由于费用急剧增加,此次覆盖相同基本医疗保健服务所需的费用额度应重新估算。
3.4 数据分析总结
上述对中国1978年后农村减贫数据的批判性分析,通过评估支撑这一信念的经验证据,挑战了关于中国自1978年以来在减少农村贫困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的普遍看法。研究发现,支持这一信念的官方统计数据因严重的时间不一致性偏差而存在深刻缺陷,这种偏差源于随时间变化的贫困标准(缩水的食物和非食物贫困线、被低估的价格指数,以及用收入和消费双重标准替代单一收入标准——非食物贫困线),以及经济改革引入的、本应被官方贫困估算考虑但未被考虑的制度变迁(医疗和教育部门的市场化,以及农村居民大规模迁移到中国城市寻找工作)。为了纠正这种偏差,本章提出了一套关于2007年中国农村贫困的替代性估算,该估算基于一种在时间上保持农村贫困标准一致并控制公共服务部门和劳动力市场中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制度变迁的方法论。
这套替代性估算与2007年的官方估算形成鲜明对比(见下文表3.13)。官方统计数据给出2007年农村贫困线为785元,而在纠正其时间不一致性偏差后,我的替代性估算指向2563.40元的水平。结果的对比是惊人的:在用2563.40元的替代性贫困线取代存在严重偏差的785元贫困线后,2007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从1479万急剧增加到2.4034亿,农村贫困发生率也从2%急剧增加到33.036%。这意味着官方农村贫困方法论中时间不一致性偏差的幅度是巨大的:农村贫困线上的偏差为1778.40元(或69.4%),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上的偏差为2.2555亿(或93.8%),农村贫困发生率上的偏差为31.04%(或93.9%)。与农村贫困线上相对较小的偏差幅度相比,农村贫困人口(93.8%)和农村贫困发生率(93.9%)上偏差幅度相对较大,是由于偏差的第六个主要来源(用收入和消费双重标准替代单一收入标准)的影响,这在估算农村贫困线时是不存在的。

将本论文的替代性估算应用于整个1978年后时期(截至2007年),将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中国在改革开放时代农村减贫的成效。
如下表3.14所示,在经济改革初期,即1978-1984年间,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大幅减少到1.28亿。同期,农村贫困人口比例也从31.6%大幅下降到15.9%。然而,此后这一趋势发生了逆转。在1984-2007年间,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增加到2.4034亿,这一水平甚至高于1978年。同期,农村贫困率也大幅上升至33.0%,同样高于1978年的水平。

表3.12中的2007a年和2007b年代表了第3.3.6节中进行的两次演算,2007b年是指在2007年替代性农村贫困线中仅包含“食物”和“非食物”要素,而2007a年是指仅将“健康调整”要素排除在替代性贫困线之外。表中与这两个年份相对应的数值清楚地表明,即使我们将一些重要因素排除在替代性贫困线之外,由此得出的(非常保守的)2007年两个农村贫困指标的数值仍将远高于去集体化结束年份(1984年)的数值。这意味着,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HRS)在中国农村全面建立以来,即使按照本论文提出的修正估算中最保守的估计,中国农村贫困状况实际上也有所加剧。
因此,关于中国自1978年以来在减少农村贫困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的普遍看法,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支持。相反,在纠正了官方统计数据中的时间不一致性偏差后,本论文得以运用一套全面的经验数据得出替代性估算,表明中国在1978年后时期的农村减贫记录很可能是一个失败,至少远未达到政府宣称和传统观念的水平。
3.5 农业去集体化的作用
本章的数据分析主要是通过调整官方农村贫困线来重新评估中国1978年后时代农村减贫的成效。它以量化方式表明,就贫困发生率而言,中国农村贫困状况可能已经恶化,或者就农村贫困居民的绝对数量而言,可能并未大幅减少。至少,本章表明,1978年后中国的农村减贫远非官方统计数据所声称的那样显著。
本章的核心分析部分是五个调整要素的确定。狭义上讲,它们涉及绝对贫困概念中必要的支出方面。农业去集体化的作用在所有这些要素中都得到了清晰的体现,尤其是在后三个要素,即健康、教育和农民工调整方面。食品和非食品日常消费品成本的迅速上涨说明了农村居民贸易条件的恶化,这反映了农业去集体化对交换领域的影响。医疗和教育服务成本的提高,在此处的替代性估算中仅部分包含,也反映了农业去集体化对交换领域的影响,因为农业去集体化导致了毛泽东时代集体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瓦解以及这些服务的商业化。农民工在城市地区额外生活费用的增加也反映了农业去集体化的一个重要影响——农民离开家乡到遥远的中国城市寻找工作。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调整因素也可以被解释为与农村贫困的收入方面有关。
首先,新估算的食物和非食物支出可作为不那么可靠的政府CPI统计数据的替代指标。这样,2007年替代性食物和非食物贫困线的高值意味着,政府报告的1978年后农村居民名义收入的快速增长水平,由于实际通货膨胀率较高,并未转化为同等高水平的实际收入。
其次,有人可以合理地辩称,尽管应采用远高于官方统计数据所示的必要支出水平作为农村贫困线,但如果普通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能够增长得更快,那么农村贫困仍然会减少。在这里,农业去集体化对自营农业收入来源(在生产和交换领域)以及对其他受雇收入来源(或工资,在分配领域)的负面影响发挥了作用。在此,作者想进一步评论工资问题。
鉴于工资相关收入在后毛泽东时代农村居民总收入中所占份额日益增加(自农业去集体化完成以来稳步增长,从1984年的14%增至2007年的27.6%——见中国国家统计局2009年,表2-12,第22页),思考这一收入来源在影响农村贫困状况方面的作用是有益的。与大多数观察者的印象相反,工资相关收入尽管稳步增长,但其仅占27.6%的份额表明,它仍然是农村居民总收入的补充来源。这深刻地揭示了农民工就业创造对农村减贫目标的影向是多么有限。如果普通农村居民可以自力更生的农业活动减弱,那么农民将被迫离开其自营的家庭农业,在分配条件不断恶化的城乡市场化和私有化企业中工作。农民工数量的增加也意味着他们在为工资停滞不前的低薪工作而激烈竞争。他们的收入如何能跟上迅速增长的必要支出呢?是的,确实为农民工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但是当健康的农业发展受到损害,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数量超过可提供的新工作岗位时,薪酬条件很可能停滞不前或恶化。这一直是农业去集体化的一个重要相关因素。
第四章 结论
4.1 主要研究结果总结
本论文旨在考察农业去集体化对1978年后中国农村贫困的影响,这一时期是以农业去集体化为起点的经济改革时代。
它将这项研究任务分解为两个分析部分。
首先,它采用比较的、历史的、制度的和以定性为导向的方法来分析从农业去集体化到中国农村贫困的因果链。这条因果链中有两个关键环节。在考察第一个因果环节时,追溯了农业去集体化对中国普通农村居民参与的三个经济活动领域——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影响。在这里,农业去集体化被视为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的深刻变革,是对毛泽东时代集体经济的彻底背离,在该集体经济中建立了一种以家庭为基础、官方称之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System, HRS)的小资产阶级经济。农业去集体化对中国农业生产的影响,既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毛泽东时代集体经济(Maoist collective economy, MCE)之间的差异角度进行了分析,也从两者在1978年后的相互作用背景下进行了分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毛泽东时代集体经济的对比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在生产领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规模经济产生不利影响,改善了约三分之一村庄的工作激励,并利用了毛泽东时代集体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遗产,但同时也限制了这些遗产的进一步发展。总体而言,农业去集体化对农业生产的净效应很可能是负面的。在交换和生产领域,在农业去集体化之后的时期,小农农业的贸易条件最终恶化,乡镇企业(TVEs)的利润与工资之比也最终上升。在考察第二个因果环节时,这些对生产、交换和分配领域的影响被转化为贫困衡量双重参数——收入和必要支出——的变化。这表明,如果毛泽东时代集体经济得以保留,收入可能不会像现在这样增长,而必要支出则有所提高。有理由怀疑农业去集体化导致了农村贫困的减少。
在这部分分析中,对两种传统观点提出了批评。首先,对毛泽东时代集体经济受到固有的激励失灵困扰的传统观点进行了严格审视,并对其提出了质疑。采用阶级分析方法来研究毛泽东时代集体经济的激励结构,以证明毛泽东时代集体经济能够为农民提供足够的劳动积极性创造有利条件。还提供了证据表明,在毛泽东时代末期,毛泽东时代集体经济总体上并未受到激励问题的困扰。大约三分之一的集体表现良好,大约40%表现尚可。然而,所有这些未受激励问题困扰的集体也被要求进行农业去集体化,其中只有少数最终成功地保留了毛泽东时代集体经济。其次,对农业去集体化在减少中国农村贫困方面发挥了强烈积极作用的传统观点进行了严格审视,并对其提出了质疑。农业去集体化对中国农村贫困的总体影响很可能是负面的,也就是说,就其本身而言,它可能增加了1978年后中国的农村贫困。
其次,本论文采用定量方法批判性地评估了1978年后中国农村减贫的成效。它指出了官方农村贫困估算中存在的几个重要偏差来源,这些偏差导致严重夸大了减贫成效。为了纠正这些偏差问题,本论文选择了国家统计局在1984年(以及1978年)采用的农村贫困标准,并将其一致地应用于2007年。在此过程中,估算了反映农业去集体化影响的五个调整要素,即食物、非食物、健康、教育和农民工,并将它们添加到2007年的官方农村贫困线中。新估算的2007年农村贫困线表明,在1978年后时期,中国农村贫困状况最坏的情况下可能有所增加,最好的情况下也不像官方宣称的那样显著。
总之,在这部分分析中,对1978年后中国农村贫困已大幅减少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批评。
4.2 启示
本论文关注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主题。其方法论和主要研究结果对经济发展和人类进步,以及社会科学学术实践具有以下启示。
首先,市场资本主义改革不仅可能导致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扩大,甚至可能导致普通民众的绝对损失。“涓滴理论”(trickle-down theory)的有效性绝对值得怀疑。经济增长本身并不能自动产生有利于穷人的过程和结果。以经济指标衡量,国有社会主义,如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国有社会主义,以及体现在毛泽东时代集体经济中的国有社会主义,并非注定失败。如果国有社会主义中的问题被解释为社会主义的问题,那么答案只能是“别无选择”,国有社会主义只能被市场资本主义所取代。然而,这种策略可能不利于普通民众的利益。如果对国有社会主义中的问题有不同的解释,那么就有可能朝着更民主、更具参与性的社会主义方向进行改革,而朝着市场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则不必垄断公共话语权。
其次,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中国农村经济的影响,可以揭示人类社会在不同生产方式选择方面的经济演进,例如封建主义、小资产阶级经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一种小资产阶级经济形式,相对于封建主义具有明显的优势。但是,将小资产阶级经济与封建主义进行比较是一回事,将其与社会主义进行比较则是另一回事。如果小农农业(或小规模家庭农场)在第三世界的许多地区确实表现出优势,那么它可能是与封建生产方式(或仍受封建主义影响的生产体系)相对照的。在这方面,就“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或国有社会主义)中可能存在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而言,在比较小资产阶级经济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时,区分国有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和封建因素至关重要。小资产阶级生产的命运也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它是否必然走向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十字路口,或者它本身就是一种稳定的生产方式?如果前者为真,那么真正的比较应该在农村经济发展领域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进行。
第三,本论文试图将定性和定量方法结合应用于一个研究课题。本论文最终成为定量和定性方法结合的产物这一事实表明,利用两者的优势可能是有益的。作者希望本论文已经证明了同时运用这两种方法对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积极价值。
注释
¹这些伴随着农业去集体化(decollectivization)而来的有记载的实际收入增长的确是惊人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农业去集体化以外的因素可能也发挥了作用。例如,在1978年至1983年间,中国(Chinese)政府将其农产品收购价格平均提高了47.7%(沃森(Watson)1989年,第393页)。
²关于贫困的某些概念,例如绝对贫困和基于收入的贫困衡量,这些概念与第二章中将收入和必要支出水平作为第二组渠道的使用密切相关,将在下文第1.3节中进一步解释和阐明。
³本论文对2007年农村贫困状况的重新估算,是基于对1984年官方估算中采用的农村贫困线标准的坚持。因此,1984年的官方估算自动保留。1978年的官方估算也与1984年的标准一致,并且不存在本论文所考察的六个时间不一致性偏差来源(详见第3.2.2节)。更具体地说,时间不一致性偏差的第一、第二和第六个来源仅在1990年代开始产生影响。第四和第五个来源与农业去集体化(decollectivization)的影响有关,在1978年并不存在。第三个来源,即不准确的价格指数,由于1978年的估算使用了实际存在的价格(而非任何价格指数)而得以避免(唐平(Tang Ping)1994年,第41页)。
4本句中用以描述绝对贫困线的“恒定”一词,指的是实际的而非名义的消费或福利水平。许多因素,例如基本消费品和服务价格的变化,或满足基本消费需求的商品和服务的可获得性的变化,或社会支付安排(即谁支付)的变化,都可能改变绝对贫困线的名义货币水平,但实际绝对贫困线不受影响。
5贫困状况改善而同时不平等状况恶化的情况可称为“温和两极分化”,而贫困和不平等状况均恶化的情况可称为“强烈两极分化”(博伊斯(Boyce)1993年,第13页)。前一种情况描述了“涓滴”效应(trickle down)理论所认为通常会发生的情况(多拉尔(Dollar)和克雷(Kraay)2002年,以及萨克斯(Sachs)2005年),而后一种情况则描述了“贫困化增长”(immiserizing growth)理论所认为可能发生的情况(格里芬(Griffin)1965年、1974年,以及格里芬和汗(Khan)1972年、1977年)。
6关于贫困差距和平方贫困差距贫困指数的具体定义和用法,参见汗和罗斯金(Riskin)2001年,第53-4页(分别称为PPG和WPG)。汗(Khan)1996年估算了中国农村地区这两个指数在1980-1994年间的值(并转载于汗和罗斯金2001年,第53页)。
7农民自产自销产品(如粮食)的价值被计算为农民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此类计算的价格随时间段和政府对市场监管程度的不同而变化。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它经历了从政府收购价格到市场价格的转变。
8随着中国(Chinese)经济的发展和/或变化,特别是由于消费模式的改变,将实际贫困线视为一个随时间变化的变量是有道理的。然而,本论文并未采用这种处理方式,原因有二。首先,对于近期农村贫困人口的确切消费模式(即消费篮子中各种消费项目的确切数量和比例)没有可用数据。其次,通常来说,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下,由此产生的农村贫困人口新的消费模式往往会导致更高的必要支出,从而推高以此方式计算的实际贫困线。因此,通过选择使用反映改革初期农村贫困人口原始消费模式的实际贫困线,得出的农村贫困线将会更低,从而对现有农村贫困状况做出更保守的估计,并对农村减贫成效做出更乐观的估计。这种处理方式将使本论文对官方统计数据的批判处于一个更合理且不那么激进的立场。
⁹因此,那些在一个时期内无需付费但在后期则必须付费的必要消费项目(如基本医疗和教育)将被纳入农村贫困线的估算中。
¹⁰例如,在缺乏安全饮用水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查找附近有安全饮用水地区的自来水和/或瓶装水价格信息来估算安全饮用水的收入等值。此外,饮用不安全的水也会增加必要的医疗费用,这同样会提高脱贫所需的收入水平。
¹¹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在资本主义经济背景下瓦解或侵蚀了凯恩斯主义(Keynesian)(以国家市场规制和资本与劳动妥协为特征)制度,而农业去集体化则在社会主义经济背景下改变了毛泽东(Maoist)制度的某些方面。然而,表征新自由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即私有化、放松管制和自由化,可以合理地用来描述农业去集体化。
¹²可以说,自由化也可能涉及农民根据市场价格和预期盈利能力决定种植何种作物的权利。但是,由于前面讨论的第二个组成部分,即管理上的放松管制,已经涉及了农民经济活动的这一方面,因此这里的自由化仅关注贸易关系本身,而不关注自由化贸易对农场管理决策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可以比作新自由主义政策组合中通常使用的放松管制和自由化之间的区别:前者涉及国内政策,而后者涉及对外政策。同理,当这两个术语被用来理解农业去集体化时,它们分别关注农场内部的管理决策和农场的外部关系。
¹³这三个层次是:1)生产队,处于最低的基层,通常覆盖一个自然村的范围;2)生产大队,处于中间层次,通常覆盖一个行政村;3)公社,处于最高层次,通常覆盖整个乡镇。尽管生产资料所有权以及集体生产和分配的组织在三个层次之间以复杂的方式进行协调,但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享有高度的自主权。
14在某些情况下,弃耕可能涉及生产力相对较低的土地。然而,这似乎并非主要因素。根据李(Li)在信中的描述,弃耕是由于小农场无利可图,因为它们无法承受日益恶化的贸易条件和不断增加的行政事业性收费。
15认为有此需求的农民可以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HRS)的基础上自发地实现这种规模经济,这似乎是合理的。然而,这里的关键在于,大单甸(Dasendian)的例子得益于国内外相关学者和非营利组织的人员、组织和资金支持,并且是后者网络的一部分。没有这些支持,这些失去毛泽东时代集体经济(MCE)组织网络的个体农户会发现组织成本高得无法承受。如果在市场资本主义环境下农民的自我组织是一个容易自发的选择,那么在20世纪50年代建立毛泽东时代集体经济的过程中,行政指导和国家管制的贸易形式的组织和经济援助就根本没有必要了。
¹⁶1952年是中国农村土地改革的结束年和社教集体化的前夜。1962年是巩固、稳定的毛泽东时代农村人民公社的起始年,生产队被确认为公社内部的基本核算单位。
17在一些关于水利设施对中国(Chinese)农业重要性的统计报告中,通常会与有效灌溉面积指标一同讨论另一个指标,即有效抗旱排涝面积。有效抗旱排涝面积在总耕地面积中所占的份额通常远低于有效灌溉面积的份额(例如,参见李保国(Li Baoguo)和彭世奇(Peng Shiqi)2009年,第25-31页)。其隐含的意思是,建设灌溉设施的最终目的是增强抵御旱涝灾害的能力。中国农业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8对于水利设施无法跟上日益增长的粮食生产需求的严重关切,在政府官员和学者中相当普遍。曹志勇(Cao Zhiyong)2006年提供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评论:“农业基础设施抵御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的能力仍未达到预期,给粮食安全战略的实现带来了诸多困难……近年来,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仅为4500亿公斤,比过去减少了约250至500亿公斤……主要原因是农田水利设施滞后。”(曹志勇2006年,第45页)
¹⁹这里的讨论主要是理论性的。随后将进行更多的经验性讨论。但在此举几个例子来说明理论观点是有益的。一个关于农民互惠行为的例子来自大寨(Dazhai)集体的历史。当陈永贵(Yonggui Chen)在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在大寨发展互助组时,为了证明互助组相对于家庭农业的优势,陈永贵自愿选择组建一个由4名老人和6名青少年组成的互助组。他是领导这个小组的唯一标准劳动年龄的成年人。他的领导策略是无私地努力工作,并通过这种方式,以榜样的力量激励其他小组成员。这个策略非常有效。那些年老或年少的其他小组成员也做出了回报,并迅速提高了他们作为一个团队的士气。结果是,这个看起来很弱的团队取得了比另一个看起来强大得多的互助组更高的作物产量。(宋连生(Song Liansheng)2005年,第6-7页)一个类似的观点是,一个可行的合作和集体参与劳动的环境可能会改变故意偷懒的心态。一个例子是,许多以前被贴上“懒汉”或“二流子”标签的村民在被吸收到互助组后成为团队工作的积极参与者。1943年,在陕甘宁边区(Sh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有4500名过去的“二流子”通过这种方式得到改造。(杜润生(Du Runsheng)2002年,第62页)
²⁰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两部早期著作中从不同角度反思了激励问题。在森1966年的著作中,他从关注狭隘自利的新古典主义视角进行理论化,认为在合作环境下,如果按需分配,工人往往会少提供劳动;如果按劳分配,则往往会多提供劳动。因此,工作积极性的关键在于在这两种不同的报酬方案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在森1977年的著作中,他批评新古典主义视角在理解个人决策时忽略了同情和承诺等重要的激励因素。本论文赞同森打破狭隘新古典主义框架束缚的旨趣。
²¹贫下中农在获得土地后仍倾向于超越家庭经营,这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他们通常缺乏劳动力和/或土地以外的其他生产资料,这迫使他们以某种方式集中经济资源,以避免经济困难和/或再次破产和失去土地。其次,由于组织成本高昂,自发的资源集中方式通常难以形成和发展,而且由于其解决由自利个体家庭引起的争端和冲突的制度能力有限,也难以维持。土地改革后农村阶级分化迹象的重新出现证明了第一点(杜润生2002年,第93-9页)。20世纪50年代初基于家庭经营的互助合作的不稳定证明了第二点(杜润生2002年,第101-3页;第124-40页)。
²²这里值得进一步解释。自耕农的家庭经营表现出两个属性,就像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方面,他们不剥削或利用其他家庭;相反,他们靠自己的劳动为生。因此,他们不会产生搭便车的动机。另一方面,自耕农不被其他家庭剥削或利用;相反,他们有权享有自己劳动的成果。因此,如果他们认为自己正在被别人的搭便车行为所利用,他们会感到受伤害,并倾向于通过怠工(或工作积极性降低)来回应。
²³这本书没有采用社会阶级分析的方法,也没有将这些家庭认定为贫下中农。然而,从书中描述的这些家庭的经济状况来看,这些农民属于贫下中农的社会阶层。
²⁴安格尔(Unger)1985年认为,政府将向生产队过渡作为基本核算单位解释为一种努力,旨在让农民看到其个人劳动贡献与其在总收益中应得份额之间的联系(安格尔1985年:第119页)。这种解释是有缺陷的。只要农业仍然是集体经营,无论核算单位的规模有多小,个人劳动贡献与个人利益之间的联系都无法建立。中国有句古老的俗语阐明了这个问题: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英文翻译是:One monk carries water on a shoulder pole. Two monks carry water together. But with three monks, there won’t be any water to drink.)。这意味着即使一个群体的人数减少到两三个人,个人劳动贡献与应得总产品份额之间的联系仍然不清楚。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应该是,通过将基本核算单位下调到生产队的水平,农民会较少关注与他们自认为的个人劳动贡献相对应的集体总产品的精确划分,也就是说,集体主义激励将被提升以抑制个人主义激励。这一点将在下文进一步解释。
25李(Li)2005年提出了一个更细致入微的案例,其中大寨模式被引入秦村(Qin Village),作为一种仅根据量化的政治态度来确定农民工分,而不考虑劳动贡献差异的方法。这种同时将政治态度转化为物质激励并放弃考虑劳动贡献的做法,对秦村的农业产出产生了不利影响。(李2005年:第92-3页)总结所有关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激励的不同案例,本作者对它们在激励农民方面的相对效力有一个初步的排序(按最有效到最无效的顺序):1. 促进集体主义激励;2. 促进个人主义激励;3. 将集体主义激励转化为额外的个人主义激励(即保留原有的个人主义激励);以及4. 将集体主义激励转化为个人主义激励(即消除原有的个人主义激励)。
²⁶戴维·茨威格(David Zweig)和威廉·韩丁(William Hinton)记录了江苏(Jiangsu)和黑龙江(Heilongjiang)两省的抵制案例,在这些地方,毛泽东时代集体经济(MCE)取得了相对较高的生产水平和机械化水平(茨威格1983年,第889-90页;韩丁1990年,第104-5页)。
27有人可能会说,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HRS)取代毛泽东时代集体经济(MCE)是一项重大的制度变革,在任何重大系统性变革的一般意义上,都应该会造成一些混乱。因此,这一重大变革本身(也就是说,仅仅因为它是一项重大变革,无论这项重大变革的内容是什么)就应该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初期的农业生产产生不利影响,这意味着早期去集体化者(或去集体化者)表现相对较差是由于这种普遍的混乱效应,而不是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毛泽东时代集体经济所造成的规模经济损失。仔细研究后,这种“混乱论”似乎并不是理解从毛泽东时代集体经济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具体过渡性质的最佳解释。首先,主流文献不支持这一论点。从传统观点来看,毛泽东时代集体经济受到激励失灵的困扰。因此,解散集体并非负面的混乱,而是对农业生产的巨大推动,因为它给予了农民更强的劳动积极性。其次,从非主流文献和本论文的视角来看,它们关注与毛泽东时代集体经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过渡相关的规模经济损失,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毛泽东时代集体经济确实造成了巨大的混乱,但这些混乱不应从一般意义上理解,就像任何重大的系统性变革一样,而应理解为由于去集体化造成的规模经济损失。这些混乱可能包括被毁坏的集体沟渠、被遗弃的拖拉机等。值得注意的是,它们是植根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结构性问题。它们的发生是因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毛泽东时代集体经济产生的规模经济相抵触。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根深蒂固之后,这些后果仍然会存在并恶化;它们不会在过渡完成几年后消失。因此,从突然过渡效应的一般意义上讲的“混乱”论点不同于“规模经济损失”论点。
²⁸然而,另一方面,早期去集体化者(或去集体化者)的表现不如晚期去集体化者(或非去集体化者)这一事实,并不一定意味着前者在去集体化之前不存在激励问题。在取消毛泽东时代集体经济(MCE)之后,也就是说,在摆脱了相关的激励问题之后,可能还有其他问题仍然阻碍着这些地区增长引擎的发展。
²⁹这些改良种子,通常被称为“高产品种”(High-Yielding Varieties, HYVs),仍然是自交系品种。最著名的是国际水稻研究所(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发明的IR8(博伊斯1993年,第61-2页)。
³⁰根据巴克利(Barclay)2007年的研究,这些品种的种质最初是由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送往中国用于培育自交系水稻品种的,但当中国研究人员测试国际水稻研究所的品系是否可以作为恢复系时,他们取得了重大突破(巴克利2007年,第23页)。中国在杂交水稻方面的成功反过来又对国际水稻研究所产生了积极影响。早在1971年,辛格·维尔马尼(Singh Virmani)博士就在国际水稻研究所开始了杂交水稻的早期工作,但很快就遇到了阻力,导致国际水稻研究所在1972年停止了杂交水稻研究。直到中国在杂交水稻方面的成功鼓励维尔马尼博士于1979年返回国际水稻研究所,国际水稻研究所才恢复了杂交水稻研究工作(奥弗雷特(Overett)2005年,第30页)。
³¹关于中国杂交水稻技术的演变和应用的详细情况,参见朱镕1988年,第87-90页。
³²值得注意的是,将当地农民纳入农业科学研究也可以通过其他制度环境来实现。例如,日本(Japan)早在19世纪明治维新(Meiji Restoration)时期就通过政府与地方农民协会的合作完成了这项任务(详情参见海部(Hayami)和拉坦(Ruttan)1980年第7章第3节)。比较日式农民协会和中式毛泽东时代集体经济(MCE)将是一个进一步的研究课题,这超出了本论文的范围。但似乎毛泽东时代集体经济代表了一种半政治性的组织当地农民的方式,而日本的方式则更以市场为基础。因此,毛泽东时代集体经济可能涉及较低的组织成本和对农民更紧密的约束。
³³本段提供的关于华容县(Huarong County)的信息和数据取自湖南省华容县革命委员会1973年,第10-4页;第28-33页。
³⁴详情参见袁隆平(Yuan Longping)2010b,第72-4页;另见龙霖庆(Long Linqing)1978年,第338页。
³⁵详情参见袁隆平2010b,第86-8页。
³⁶详情参见袁隆平2010b,第88-9页。
37详情参见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农业局1978年,第45-65页,第65-7页。值得注意的是,存在一种推测性论点,认为“四自一辅”(four selfs, one supplement)的政策不能应用于杂交水稻种子的生产,因为后者涉及昂贵而复杂的程序(吴贤智(Wu Xianzhi)1984年,第32页)。然而,本段描述的湖南省(Hunan Province)在20世纪70年代的经验表明并非如此。
38根据2010年底的一则新闻报道,2010年四川(Sichuang)杂交水稻种子的平均市场价格为41.1元/公斤(中国农资网(Zhongguo Nongzi Wang)2010年)。同一篇报道预测,2011年价格将上涨20-30%。根据2011年底的另一则新闻报道,2011年的实际价格涨幅为10-17%(神农网(Shennong Wang)2011年)。因此,根据上一年的估计,2011年的实际市场价格可能在49.3-53.4元/公斤左右,或者根据年末的报告,在45.2-48.1元/公斤左右。政府设定的2011年价格上限为45元/公斤。
³⁹世界银行(World Bank)也有一套统计数据,对公众关于中国农村减贫成效的认知产生了广泛影响。然而,鲜为人知的是,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也是基于中国国家统计局(NBS)进行的农村住户调查。唯一的主要区别在于应用了国际贫困线(例如每天1美元),并且为了适应这一标准,在美元-人民币转换中使用了购买力平价计算。
40不同研究者关于国家统计局系统衡量中国农村贫困年份的说法略有不同(唐平1994年;陈(Chen)和拉瓦利он(Ravallion)1996年;帕克(Park)和王(Wang)2001年;以及王等人2006年)。本文采用帕克和王2001年的说法,因为它是最详细的,并且与其他说法的矛盾之处最少。
41其他一些描述贫困状况的常用指标,尽管不如贫困发生率(贫困人口比例)常用,包括贫困差距指数(贫困深度)和加权贫困差距指数(贫困严重程度)。详情参见汗(Khan)和罗斯金(Riskin)2001年,第53-4页。
42值得注意的例外是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na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 CHIP)背后的独立研究人员,该项目从1988年开始每七年在中国农村进行一次定期调查。特别是,汗1996年和汗与罗斯金2001年给出了一些关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农村贫困的替代性估计。然而,现有文献中仍未努力提出整个1978年后时期的替代性估计。
43尚不清楚国家统计局为何选择在1998年改变热量摄入标准。一个合理的猜测可能是国家统计局故意这样做以降低贫困线。但人们可能会问另一个问题:如果国家统计局试图降低贫困线,那么为什么国家统计局同时又将消费模式标准从每日摄入低于2400千卡路里的人群的消费模式改为年收入低于800元的人群的消费模式,这远高于1998年的官方农村贫困线(635元)?同样不清楚国家统计局为何选择800元而不是635元,但有两点是明确的。首先,国家统计局不可能仅仅因为635元是1998年的农村贫困线就选择收入低于635元人群的消费模式。为什么?仅仅因为在完成前面讨论的所有这些步骤(最初的步骤之一是确定消费模式)之前,你还不知道农村贫困线是多少。其次,如下一个脚注所解释的那样,即使是1998年收入低于800元人群的消费模式,其食物选择仍然比1984年每日摄入2400千卡路里的人群更便宜。本章末尾还将表明,尽管800元高于1998年的官方农村贫困线(635元),但它很可能仍远低于1998年更合理估计的贫困线。因此,通过这种方式改变消费模式标准,国家统计局仍然可以达到降低农村贫困线的效果。
44 1998年人均收入低于800元的家庭平均消费结构包括219.61公斤谷物和8.90公斤肉类(中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第39-42页)。与1984年的标准(220公斤谷物和9.24公斤肉类)相比,1998年的消费模式肉类份额较低,谷物份额较高。鉴于肉类价格远高于谷物价格,1984年的消费模式涉及更昂贵的食物选择。
45中国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首席宏观经济分析师万小西(Xiaoxi Wan)估计,2005年中国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应为1978年的15至50倍,即官方公布数字的3至10倍(根据官方数据,2005年中国城市CPI是1978年的5.031倍)。详情参见万小西2006年。这一研究结果随后在网上广泛流传,甚至在已发表的著作中被引用并得到认可(例如,参见郑建人(Zheng Jianren)2007年和徐一胜(Xu Yisheng)2009年)。万的估算被广泛赞誉为与中国城市普通居民在1978-2005年期间的真实经历相符。
46如果我们消除子构成部分之间的任何重叠,那么根据1998年的方法论,农村贫困人口由三组人构成:(1)收入和消费均低于贫困线的人;(2)收入低于贫困线但消费在贫困线1.0至1.5倍之间的人;以及(3)收入在贫困线1.0至1.5倍之间但消费低于贫困线的人。相反,根据1984年的方法论,仅考虑收入标准,农村贫困人口的三个子构成部分是:(1)收入和消费均低于贫困线的人;(2)收入低于贫困线但消费在贫困线1.0至1.5倍之间的人;以及(3)收入低于贫困线但消费高于贫困线1.5倍的人。1998年的方法论与1984年方法论的前两个子构成部分相同,同时减去了后者的第三个子构成部分,并增加了一个新的子构成部分(1998年方法论的第三个子构成部分)。
47《中国国家统计局2009》中发布的2007年农村贫困发生率(1.6%)与本文表1中提供的数字(2.0%)不同,后者也基于国家统计局的来源。由于贫困发生率部分取决于农村总人口数量,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不同国家统计局来源中的农村总人口数量不同。由于《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中国国家统计局2007年、2008年、2009年)没有提供农村总人口的明确数据,这导致我使用《中国国家统计局2010》的农村总人口数据。
48这里必须澄清为什么本论文选择固定的食物篮和固定的食物与非食物比例。理想情况下,用于计算贫困线的食物篮或消费模式应随时间进行修改,以反映贫困人口不断变化的消费行为。的确,即使贫困人口满足了每日2400千卡路里的相同热量摄入,他们也可能消费不同的食物组合,尤其是在几年过去之后。但是,由于数据可得性的限制(仅有关于1984年每日摄入2400千卡路里人群的食物篮或消费模式的详细信息),本作者无法调整2007年的食物篮。因此,最佳策略是坚持使用1984年的标准。然而,本作者确实意识到了由此可能产生的偏差。由于大约三十年来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国农村地区每日摄入2400卡路里的人群很可能已经转向比1984年更昂贵的食物组合。因此,通过坚持使用1984年的旧食物篮,本论文对2007年农村贫困线的估算可能存在向下的偏差,这将低估2007年的农村贫困状况。因此,由此得出的估算结果更应被视为一个保守的估计,即2007年农村贫困的底线(“至少有这么多贫困”)。选择1984年采用的固定食物与非食物比例(60:40)也是由于数据可得性的问题,并且很可能与固定食物篮产生相同的效果:随着长时间的快速经济增长,食物支出占非食物支出的比例趋于下降;因此,坚持固定比例往往会导致估算的农村贫困线出现向下的偏差,从而低估农村贫困状况。再次强调,尽管这是一个有偏差的选择,但它可能很好地服务于本论文的目的,因为由此产生的估算结果作为对官方统计数据和传统观点的保守(或底线)批评,将具有更强的自我辩护能力。
49有理由相信这个新制度正在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改善,因此2007年的有效报销率应该高于2005年。然而,在2005年,这个新制度仍处于早期试点阶段。它将在2010年覆盖整个中国农村地区。总的来说,使用2005年试验地区的有效报销率(3.42%)作为2007年整个中国农村地区的比率可能有些道理。
⁵⁰关于将此健康调整项加入农村贫困线的进一步说明,见下文第3.3.6节,第143-6页。
51见2005年12月28日新闻报道,网址:http://news.sina.com.cn/c/2005-12-28/10207839503s.shtml。
52《人民日报》,2008年3月4日,第1版。网址:http://finance.people.com.cn/GB/6952067.html
53这两个数字来自国家统计局关于2009年农民工状况的报告。网址:http://www.stats.gov.cn/tjfx/fxbg/t20100319_402628281.html
54这里有一个假设:城市务工农民在整个农村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与城市务工农民在农村贫困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相同。由于贫困的城市务工农民的百分比可能大于城市务工农民在整个农村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因此这个假设可能会低估农民工调整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