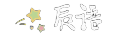暂无AI摘要
暂无AI摘要 脱胎换骨曾国藩。
晚年曾国藩总结自己的人生体会说,人的一生,就如同一个果子成熟的过程。
不能着急,也不可懈怠。
青年时的他是蠢笨的庸才,30 岁后,改变气质,增长本领,脱胎换骨。
一、三十岁前是庸人
曾国藩的老家是湖南省湘乡县大界白杨坪。
地处离县城一百三十里的群山之中,虽山清水秀,风景不恶,但交通不便,消息闭塞。
曾国藩在诗中说这里「世自痴聋百不识,笑置《诗书》如埃尘」。
二○○八年四月,我去探访这个地方,发现它到现在似乎也不怎么需要与外界打交道,班车次数极少。
我从韶山出发,居然辗转颠簸了整整一天,换了五次车(包括摩的),才到达这里。
在晚清时代,这里的闭塞程度更可想而知。
在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之前,几百年间,这里连个秀才也没出过。
不但「无以学业发明者」,也没有出现过大富大贵之族,可以说是一处被世界所遗忘的角落。
传统时代,农民们想要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困窘生活,几乎只有供子弟读书一途。
曾国藩祖父曾玉屏中年之后的全部期望就是子孙们靠读书走出这片天地。
他不惜血本,供长子曾麟书读书,「穷年磨砺,期于有成」。
然而,曾麟书资质实在太差,虽然在父亲的严厉督责下,兀兀穷年,攻读不懈,却连考了十七次秀才都失败了。
作为长孙,曾国藩身上背负着上两代的希望。
然而曾家的遗传似乎确实不高明,曾国藩从十四岁起参加县试,也是榜榜落第,接连七次都名落孙山(曾国藩的四个弟弟也没有一个读书成功)。
曾家已经习惯了考试失败后的沮丧气氛,他们几乎要认命了。
然而,二十三岁那年,曾国藩的命运之路突然峰回路转。
这一年他中了秀才,第二年又中了举人。
又五年之后的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年),二十八岁的曾国藩中了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
老曾家一下子老母鸡变凤凰,成了方圆几十里的第一大户。
虽然跃过了龙门,但此时的曾国藩整个眼眶里只装得下出人头地、光宗耀祖。
从气质到观念,与其他庸鄙的乡下读书人并无本质不同。
在白杨坪这个小天地里成长起来的曾国藩全部精力都用在八股文上,朝夕过往不过是些鄙儒,其中甚至还有「损友」。
进京为官以前,曾国藩耳目所闻的,不过是鼓吹变迹发家的地方戏;头脑中所想的,不过是当官发财,给家里争口气。
好友刘蓉说他当时「锐意功名」,他自己也说当时最大的心事不过是「急于科举」。
在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年)的一封家书中他说:「兄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兴庸鄙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
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因为人毕竟是被环境决定的。
道光二十年(一八四○年)正月二十八日,曾国藩结束在家「把戏」,抵达北京,开始了漫长的官宦生涯。
刚过而立之年的曾国藩和每个普通人一样,有着大大小小许多缺点。
一是心性浮躁,坐不住。
曾国藩天生乐于交往、喜欢热闹,诙谐幽默。
在北京头两年,他用于社交的时间太多,每天都要「四出征逐」,走东家串西家,酒食宴饮,穷侃雄谈,下棋听戏。
虽然他给自己订了自修课程表,但执行得并不好,认真读书时间太少,有时间读书心也静不下来。
道光二十年六月,曾国藩在日记中说,四月份「留馆」之后,他「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憩,不觉过了四十余天」。
他总结自己在四十多天内,除了给家里写过几封信,给人作了一首寿文之外,「余皆怠忽,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
因此,他在日记中给自己立了日课,每天都要早起,写大字一百,温习经书,阅读史籍,还要写诗作文。
但这个日课并没有严格执行,虽然比以前用功了些,但他还是经常「宴起」,喝酒,聊天,下棋,出门拜客。
比如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年)七月十日记载,早饭后,张书斋、曾心斋两位朋友先后到他家来聊天。
送走他们后,他写了十行字,又出门「拜客数家」。
然后又赴宴,与七个朋友一起饮酒吃饭。饭后又去小珊家,一直聊到深更半夜才回家。
这一天所有的「成绩」就是十行字。
翻开日记,责备自己「宴起」「无恒」「太爱出门」的记载到处都是:
无事出门,如此大风,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
说话又多戏谑……
应酬稍繁之际,便漫无纪律……
心浮不能读书……
自定课程,以读《易》为正业,不能遵守,无恒……
读书悠忽……
自窥所病,只是好动不好静……
醒早,沾恋……
晏起,则一无所作,又虚度一日,浩叹而已……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二是为人傲慢,修养不佳。
虽然资质并不特别优异,但曾国藩在湖南乡下朋友圈里总算出类拔萃,并且少年科第,所以一度顾盼自雄。
在离家到京任官之际,他那位识字不多却深有识人之明的老祖父送给他这样的临别赠言:「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尔若不傲,更好全了。」
老祖父的一句箴言当然不足以扫平他身上的处处锋芒。
在北京的最初几年,「高己卑人」,「凡事见得自己是而他人不是」这最常见的人性缺陷在他身上体现得很明显。
他待人接物,不周到之处甚多。
他的几个至交都曾直言不讳地指出他的「傲慢」。
他的好朋友陈源兖就告诉他:「第一要戒『慢』字,谓我无处不著怠慢之气。」「又言我处事不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须步步留心。」
第二个是「自是」,听不进不同意见,「谓看诗文多执己见也」。
因为修养不佳,脾气火暴,曾国藩到北京头几年与朋友打过两次大架。
第一次是与同乡、刑部主事郑小珊因一言不合,恶言相向,「肆口谩骂,忿戾不愿,几于忘身及亲」。
另一次是与同年兼同乡金藻因小故口角,「大发忿不可遏,……虽经友人理谕,犹复肆口漫骂,比时绝无忌惮」。
这几句描写形象地描绘了曾国藩性格中暴烈冲动的一面。
普通人在社交中最容易犯的错误是言不由衷,语涉虚伪。
比如在社交场合常顺情说好话,习惯给人戴高帽子。
比如自矜自夸,不懂装懂,显摆自己,夸夸其谈。
人性中这些常态在曾国藩身上一样存在,甚至更突出。
畏友邵懿辰指出他的第三个缺点就是「伪,谓对人能作几副面孔也」。
在曾国藩日记中,他多次反省自己的这个缺点。
比如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十月初四,朋友黎吉云来拜访,「示以近作诗。赞叹有不由衷语,谈诗妄作深语」。
赞叹之词并非发自内心。
而且聊着聊着,自己就故意显摆高深,夸夸其谈起来。
这样的记载数不胜数:
酒后,与子贞谈字,亦言之不怍。
客来,示以时艺,赞叹语不由衷。予此病甚深。
学中无所得,而以掠影之言欺人。
又说话太多,且议人短。
席间,面谀人,有要誉的意思,语多谐谑,便涉轻佻,所谓君子不重则不威也。
对于一般人来说,这是无伤大雅的社交习态,如同喝汤时不小心会出声一样,几乎人人不能避免。
但对于圣人之徒来说,却是相当严重的问题。
因为儒家认为,修身之本在于「诚」。
对自己真诚,对别人真诚,一是一,二是二,一丝不苟,才能使自己纯粹坚定。
适当的「善意谎言」是社交必不可少的润滑剂,但当言不由衷成为习惯时,「浮伪」也就随之而生,人的面目也就因此变得庸俗可憎。
除了以上三点,曾国藩认为自己还有一大缺点,必须改过,那就是「好色」。
今天看来,这似乎有点可笑。
血气方刚、刚过而立的他,见到美女自然会多看几眼。
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本能反应。然而用圣人标准一衡量,问题就严重了。
曾国藩日记中多次记载自己犯这样的错误:
在朋友家看到主妇,「注视数次,大无礼」。
在另一家见到了几个漂亮姬妾,「目屡邪视」,并且批评自己:「直不是人,耻心丧尽,更问其他?」
不但多看他人妻妾不能容忍,甚至对于自己的夫妻恩爱,曾国藩也战战兢兢。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对「欲望」特别是对「色」的恐惧是一个特别的底色。
中国人普遍认为,纵欲,特别是沉溺于「色」,是斫伐根本的危险之举。
曾国藩身体一直不太好,所以认为自己有必要厉行节欲。他说自己「明知体气羸弱,而不知节制,不孝莫此为大」。
当然,这种节制在某些年纪是很难的。
所以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四,他为此大骂了自己一次。
那一天他早起读了读书,没有所得,而「午初,人欲横炽,不复能制」,做了「不应该做」的事,遂骂自己「真禽兽矣!」
二、「脱胎换骨」
三十岁是曾国藩一生中最重要的分水岭。
曾国藩之于后人的最大意义是,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一个中人,通过「陶冶变化」,可以成为超人。
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真诚地投入自我完善,他的本领可以增长十倍,见识可以高明十倍,心胸可以扩展十倍,气质可以纯净十倍。
愚钝之人,通过自我磨砺,也可以看得透,立得定,说得出,办得来。
浮嚣之人,也可以变得清风朗月般从容澄净。
偏执之人,亦可以做到心胸开阔,不矜不伐。
道光二十年入京为官,不仅是曾国藩仕途上的起步,也是他一生自我完善的一个重要起点。
作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北京聚集了当时顶级的人才,而翰林院更是精英之渊薮。
一入翰苑,曾国藩见到的多是气质不俗之士,往来揖让,每每领略到清风逸气。
他在写给诸弟的信中兴奋地介绍说:
京师为人文渊薮,(朋友)不求则无之,愈求则愈出。
现在朋友愈多:讲躬行心得者则有镜海先生艮峰前辈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
穷经知道者则有吴子序、邵蕙西;
讲诗文字而艺通于道者则有何子贞;
才气奔放则有汤海秋;
英气逼人,志大神静,则有黄子寿。
又有王少鹤……朱廉甫……吴莘畲……庞作人。
曾国藩发现,这些人的精神气质与以前的朋友们大有不同。
他们都是理学信徒,有着清教徒般的道德热情。
他们自我要求严厉峻烈,对待他人真诚严肃,面对滚滚红尘内心坚定。
这些朋友给了他极大的影响:
近年得了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
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马迁、韩愈这样的大学者亦可学而至也,程亦可学而至也。
三十岁前曾国藩的人生目标只是功名富贵、光宗耀祖。
结识了这些良友之后,他检讨自己,不觉自惭形秽,因此毅然立志自新:
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弟之先导。
正是在三十岁这一年,曾国藩立下了「学作圣人」之志。
「圣人」是儒学信徒的最高生命目标。
人类最基本的一种心理倾向就是使自己变得完美。
中国儒、释、道三家,对生命目标的设计都是极其超绝完美的。
道家认为,人通过修炼,可以不食五谷,吸风饮露,逍遥无恃,长生久视,与天地同,成为「至人」「真人」「神人」。
佛教则认为人皆有佛性,通过自修,都可以达到不生不灭、断尽欲望的佛的境界。
儒家自然也不例外。
儒家的圣人理想,其完美与超绝不下于神仙或者佛陀。
儒家经典说,所谓「圣人」,就是达到了完美境界的人。
圣人通过自己的勤学苦修体悟了天理,掌握了天下万物运行的规律。
因此可以「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明并日月,化行若神」。
他的一举一动,无不合宜,对内可以问心无愧、不逾规矩,对外可以经邦治国,造福于民。
这就是所谓「内圣外王」。
超自然的夸张固然过于虚幻,不过,除去这些缥缈的因素,儒家的「圣人」理论毕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可操作性的人格理想,其中有着符合人类基本心理经验的合理内核。
马斯洛将人的需求分成五个层次。
第一层是食色性也,第二层次是安全的生存环境,第三层次是人际交往的需要,第四个层次是功名荣耀、出人头地。
最后一个层次是自我实现。
所谓自我实现,就是将自身的生命能量燃烧到最充分,把自己变成一个大写的人。
儒学的圣人理想,基本上可以类比为马斯洛所说的「自我实现」。
确实,儒家的「圣人状态」与马斯洛所说的自我实现后的「高峰体验」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
人的巨大潜力往往是人类所不自知的。
所谓庸人,就是昏睡了一生的人,因为欲望缠绕,意志软弱,智慧不明,普通人一生只能动用上天赋予的很少一部分潜能。
而英雄伟人则是醒过来的人,他们天性刚强,头脑有力,可以把自身潜能发挥得比较充分。
而「圣人」,或者说达到「自我实现」状态的人,则是通过刻苦努力,穿透重重欲望缠绕,战胜种种困难,将自身潜能调动发挥到近乎极致。
儒家说,一个人修炼到了圣人状态,就会「无物,无我」,「与天地相感通」。
就会「光明澄澈」,「从容中道」,达到一种极为自信、极为愉快的情感状态。
而马斯洛也说,当一个人充分自我实现时,也会体验到一种难言的愉悦,欣喜若狂、如醉如痴。
人在这时最有信心,最能把握自己、支配世界,最能发挥全部智能。
在高峰体验中主客体合一,这是人的存在的最高、最完美、最和谐的状态。
应该说,儒家的圣人理想远比马斯洛的「自我实现」高远和超越。
马斯洛给人实现自己的自然本能以充分的空间,而儒学要求以抽象的由「天理」构成的人,取代具有庸常情感的自然人。
因此,儒家的圣人理想有着非理性的、反人性的一面。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圣人学说」也不失为一个强大的心理武器。
所谓「取法乎上」,它确实给传统的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可以调动起全部潜能的奋斗目标。
只不过,儒家学说所设定的自我完善目标如此高远和超越,几乎不可操作。
由于目标的高远难及,手段便非同寻常。
从曾国藩身上,我们可以悟出自我完善的必经途径。
首先是立坚韧不拔之志。
立志对一个人人格发展的意义是决定性的。
人的巨大潜力往往是人类所不自知的。
心理学家费约做过这样一个实验。
他要求三群学生举起重物,看谁坚持的时间长。
他对第一群人什么都没有说。对第二群人说的是,想看看你们谁最有耐力。
对第三群人,他则说,你们举起的这些东西关系重大,因为上面的导线连着一个电网。
如果你们一放下手,这个城市就要断电。为了朋友和家人们,你们一定要多举一会儿。
结果,第一群人平均举了十分钟,第二群人竭尽全力,平均坚持了十五分钟。第三群人,却平均坚持了二十分钟。
可见,人的能力发挥多少,与对自己的要求是密切相关的。
或者说,精神力量直接决定着身体潜能的发挥程度。
因此,「立志」或者说确立一个终身的奋斗目标,对一个人的精神成长是至关重要的。
曾国藩对这一点体认极深。
他曾说过,立志譬如打地基。
「古者英雄立事,必有基业。……如居室然,宏大则所宅者广,托庇者众。诚信则置趾甚固,结构甚牢。」
只有基础广阔、结实,才能在上面盖起宏伟壮大的生命之殿。
曾国藩人生第一个成功之处,就在于立了最高远的志向。
马斯洛将自我实现列为人的最后一重追求。
越过从食色性也到出人头地这些层次,才能达到自我实现。
而曾国藩直接把目标锁定在了自我实现,也就是做「完人」。
他认为,这一目标实现了,其他目标就自然而然地能达到。
他在给诸弟的信中说,不必占小便宜:「做个光明磊落神钦鬼服之人,名声既出,信义既著,随便答言,无事不成,不必爱此小便宜也。」
也就是说,如果做成了光明磊落的伟人,人生日用、建功立业自然也就不在话下。
道光二十二年,曾国藩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他已经立定了终身之志。他说: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
这就是他为自己立定的「终身大规模」。
以「完人」为人生目标,确实可以称得上是「取法乎上」了。
曾国藩一生成功的第一个要诀,就是立志高远。
这一志向,驱动他一生不在小诱惑、小目标面前止步。
促使他在多大的困难面前都不苟且,不退缩。
促使他「洗除旧日晻昧卑污之见,矫然直趋广大光明之域,视人世之浮荣微利,若蝇蚋之触于目而不留」。
有了志向,接下来需要的就是实行力。
古往今来,立志之人比比皆是,但是真正实行的人,却是凤毛麟角。
曾国藩的真正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脚踏实地地实践了自己的志向。
从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立志自新之日起,曾国藩开始了对自己全方位的改造。
他的办法是「日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