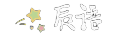暂无AI摘要
暂无AI摘要 对于那些乐于从时空两方面探测生命的长度与宽度、通过纵横两条线索去探寻文化与文化互相交融又互相掣肘的关系、总爱在生活诸多场景和时间节点上畅言“世事业已看惯,此心到处悠然”、在代沟、学业、抑郁症、孤独之间彷徨却又以自由为美以光影为梦的人来说,昙华林算得上是一个相当有吸引力和意义的去处。在诸多武汉人看来,汉口铜臭味太浓,汉阳有点偏僻却偏偏将宗教、军事和音乐杂糅在一起,比如古琴台,归元禅寺,汉阳兵工厂等拼凑在一起,多少有点不伦不类,却又逼人前去参观游览。那武昌呢?当然人文气息就要浓许多,不仅仅武汉大学等名校赫然在列,更重要的是,昙华林在那儿。历来古刹多隐于山野林间,太过清幽、孤寂、安静、逍遥和清贫,而众多一手高举极端物质化甚至鲜廉寡耻的生存法则,一手高举清高、傲慢、自负和文化大旗的知识分子,多崇尚“大隐隐于市”的生存或隐居方式。如果将昙华林看成是这样的人士或现象,也算是贴切的。
时间深处的昙华林早先是指与武昌戈甲营出口紧密衔接的东面地界,一条苍老、古旧、恬静、时尚、悠闲、不长也不短的街道,后来,也就是一九四六年官府将戈甲营西面的正卫街与游家巷与它合并,统称为昙华林。关于“昙华林”作为街道之名的由来,我查询过资料,也询问过相关人士,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版本。首先,与宗教的关系。郭沫若曾经在他的一部著作中提到,“昙华林”很可能与佛教有关,“昙华”二字是印度梵文的音译,“林”乃“居士林”的简称。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尽管没有取代道教和儒教,但发展之迅猛,不必赘述,僧侣们建造的寺院,都有“丛林”之说,很多寺院大多自诩为“震旦第一丛林”。第一不第一很次要,重要的是苦修苦行之地,都是“林”。其次,据说街道和小巷子内居住着很多种花人,他们种植的花卉品种繁多,到处都是,且一坛一花,“坛”“昙”同音,便有了昙华林之说。第三,巷内多花园,园中众多花卉中尤以昙花为最,年年种植,精心呵护,犹如花的海洋,花的丛林。古汉字中“花”“华”皆指植物之精华,即花,且两字通用,就有了昙华林之名。有了这名分,昙华林从时间的深处冒出来,露出了它与众不同的模样和神采。来来去去的人,便顺遂了时间的指引,从中山路开始,慢悠悠软哒哒地走到西边的得胜桥,慢悠悠软哒哒的光阴慢慢变成内心的感应。匆匆而来的人,看过后会慢慢离开,离开了的人,在外面倏忽即逝的快节奏生活折磨中,便有了怀念,便会在某个时段放下一切,重新来到昙华林,再次慢慢悠悠地从东到西,或从西到东,所有曾经深埋于光阴尘土之中的建筑,都向他们打开了门,不管是医院、校舍,还是教堂,你可以进去悉心观摩,也可以飘然而过,而在缓慢悠长的街面上,你什么人事都可以思量,也可以不加理会,身边的人全然陌生,却又似曾相似,冰冷的脸色或缤纷的笑意,都与昙华林有关。
首先得说说西方人在昙华林留下的建筑。西方人打开满清和后来的中华民国的大门,除了枪炮、战舰、鸦片、唧唧哇哇的语言和毛耸耸的肢体之外,就是宗教,而在全国各地建造的教堂,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文明之间的互相渗透、包容、欣赏和礼遇,传教士们的教义,并非都是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服务的,很多富有人性化的元素,是宗教的中心涵义。很多在华的西方教会,还有后来涌进中国的西式快餐,比如麦当劳肯定德基等,在人文关怀,尤其是在对待穷苦人、孤旅者和流浪汉方面,比咱们的很多官方机构和民间机构要有人情味得多。当然,西式教堂的终极意义,大抵还是为侵略服务的,这个不可否认。在昙华林,西方宗教进入的日期是一八六一年,也就是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在龚自珍的儿子龚半伦的带领下,火烧圆明园的那一年。之前,昙华林的宗教形式主要是本土宗教道教,自然也少不了佛教,但在西方宗教入侵之后,道教和佛教便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最终在昙华林占据一席之地,设立教区的国家主要是有瑞典、美国、英国和意大利。英国凭借的是它作为“日不落帝国”在海洋上的霸权,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熔炉,最发达的国家,能够长时间在昙华林活动,不难理解,而瑞典和意大利也来小走小活一段时间,确实让人意外。但仔细一想,尽管有军事实力的差异,但西方国家在民生和海外扩张方面,并不像军事实力的差别那么大,枪炮开了道,什么人都涌进了积贫积弱的中国,实在是正常之事。这些教区分别为:以螃蟹岬为中心区域的瑞典教区;以昙华林正街为中心的美国教区;以花园山为中心的意大利教区;以戈甲营为中心区域的英国教区。所属每个教区的建筑有与其国家的文化相符合,这些建筑中,既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与文明,尤其是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极其吻合的,乃教堂。这些教堂中,瑞典教区的教堂维护得较好。教区大门左侧是一株看起来颇有些年月的英国梧桐,枝叶婆娑,枝干粗壮。大门是中式风格,牌楼形状,门额上用汉字题写着“瑞典教区”四字。过大门,是一道门廊,不长,进去,便是瑞典教区的主建筑群,建造于一八九零年,典型的北欧建筑风格。建筑有二层、四层,砖木结构,所有楼房外面的柱廊都是券拱型的。据资料记载,瑞典教区是瑞典基督教行道会在湖北的总会驻地,建筑主要分为主任牧师楼、基督教道路堂和真理中学等。抗战时期,瑞典驻武汉领事馆迁入瑞典郊区,除了主理本国各类外交事宜外,还代理英美等西方国家与武汉汪伪政权之间的事务。一九五二年,瑞典领事馆关闭,瑞典人在武汉,尤其是在昙华林的历史使命到此终结。如今的瑞典教区,保存相对完好,游客可以参观、拍照。但最显眼的两栋建筑显然无法抗拒时间的侵袭,露出沧桑、颓废的样子来。但不管怎么说,瑞典教区旧址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教会旧址,都是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互相碰撞和交融的一个见证,建筑和宗教两个元素,在某种程度上也见证了中国社会和文明的进程,只是这些进步和发展,有时充满了血腥味道的,有时是温和的,更多的,还是文化的,最终与世界文明互相呼应,却又各自独立。
昙华林纯西式风格的建筑还有崇真堂,花园山教堂,位于中医药大学内的圣诞堂和育婴堂万婴墓等。崇真堂在街道戈甲营四十四号,距出口不远。遗憾的是,铁门紧闭,旁边有一牌子,自上而下写着“武汉市基督教崇真堂”。崇真堂的主体建筑呈平面拉丁字形,哥特式建筑风格,仅一层,容量约六百人。据说这是英国基督教徒(基督教伦敦会)杨格非于一八六四年雇人建造的,是基督教在武汉建造的第一座教堂,也是西方宗教在武汉“侵入”的发端,历史悠久,美学和历史价值不低。矗立在花园山上的诺撒仁修女会教堂也是昙华林重要的宗教建筑,主要从事公益事业,颇有口碑。现在武汉市儿童福利院的前身是育婴堂万婴墓,由艾原道主教创办于一九二八年,并由德国籍女性长期主持,将收进的婴儿送到外面,雇请奶妈养育。一九二九年圣若慧善功修女会成立,继续加强育婴堂的工作,享有一定的社会声誉。但因一九五一年育婴堂大量死人现象被披露,引起广泛社会关注,并由政府接管,进行整顿,并修建了万婴墓,将死者骸骨埋葬于该墓,并在旁边竖立“死难婴儿纪念碑”。育婴堂创立的初衷原本就是养育被抛弃的婴儿,乃一桩善事,但大量婴儿死亡的现象,不得不令人深思和感到遗憾,这也成了该堂挥之不去的阴影,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尽管有诸多资料进行了披露,但真实的情形和诸多细节,还是只有当事人知晓。历史,恐怕就是这样在阴差阳错中演绎的,无数事实泥牛入海,我们只能在残存的遗迹上,挖空心思去想像,但依旧与真相相隔很远。
西方人来到东方,还带来了他们的医学,而且跟宗教联姻。在武汉的众多医院中,西式医院多为教会医院,是宗教的另外一种演绎形式,大致意思无外就是拯救众生,从肉体到灵魂,精神到思想等。昙华林的西式医院以仁济医院为代表,乃一所典型的西式医院,由中华基督教会和英国基督教伦敦教会慈善机构共同创建,原名英国伦敦会医院,具有强烈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风格。资料上说,该医院为砖木结构,上层为简化了的多立克柱廊,底层为连续的罗马券柱廊。医院门诊部呈平面矩形,两层,上下四周回廊环绕,结构紧凑。辅楼呈凹形,中为下沉式庭院,这种庭院建造样式,是典型的中国式样建筑模式,尤其是其中的下沉式回廊,与门诊部的文艺复兴式的回廊相得益彰。仁济医院的前生是一八六一年英国公理宗伦敦会传教士杨格非在戈甲营建造的礼拜堂,之后又创办了一家诊所和一座义塾,义塾于一八六八年迁到昙华林,加以扩建后,在一八八三年将诊所改为“仁济医院”。尽管欧洲列强入侵中国,从身心两方面伤害了中国人,尤其是鸦片的输入,但从大量创办教会医院等举措,也对中国人的身心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抚慰和医治,同时,也对自恋得相当可以的中医提出了挑战。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在医学方面是持久的,至今仍有不少的人,跟五四时期的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一样,全盘否定中医,而笃信中医的人,又极力否认西医的功效和价值,互为敌人。不过,不管中医,西医,在治病救人等方面是殊途同归的,中医沾沾自喜的哲学人学医学等文化体系,西医视为命根的科学性和实验性,本质上差别不大。
徜徉在这些几乎就要被世人遗忘,被时间吞噬,却始终不曾消亡的建筑之间,无不让人醉心于历史源源不断的演变之中。当我们进入于我们的本土文化相粘连的建筑中时,对历史的感觉和思考会更加强烈和深刻。比如,朴园,乃钱钟书父亲钱基博先生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朴园是当时武汉私立华中大学(即现在的华中师范大学)的公寓之一,建造于一九三六年,最先居住于此的是一个美国教师,抗战时期,日本人进占武汉,朴园成了日本人的宪兵司令部,抗战结束后,钱基博先生搬到这里来,居住了十一年,也是他人生的最后十一年。如今,钱老先生的居住的房间改成了文艺沙龙,据说很多搞艺术的师生来此喝咖啡,畅谈艺术。我对这种既是故居,又是文艺沙龙的方式并不以为然,叨扰仙逝之人的安静,毕竟是一桩不合时宜的事情,虽说故居和沙龙之间并不矛盾,艺术终归是要接地气,接历史的,但看到一些从学院中来的中年人青年人有一搭没一搭地在钱老爷子的故居里说说笑笑吃吃喝喝,还是感到非常别扭。在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旧址前,我彷佛看到了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真真假假的蜜月期中,郭沫若等人在这里辛苦工作的情形。外敌当前,抛弃前嫌,一致对外,是大的策略,战略,但国共两党其实都清楚小日本不可能在中国打持久战,最终的争斗,还是在一家人中展开。事实上也是如此,老蒋被踢到台湾,这些那些旧址,尽管在沧桑岁月中变换着模样,但它们依旧是要说话的,会说话的。会说话的,而且是用佛的名义说话的,还有那个忠义的福建人翁守谦。关于满清时期的战事,尤其是海战,资料不少,写的,评论的人和文章很多,除了哀叹,还是哀叹。哀叹完了,骂几声满清的无能,就再也没有言语了。但翁守谦老先生还是值得写写的。作为满清北洋水师的官员,他在甲午战争中是有作为的,有功劳的,即使历史典籍的记载不甚详尽,但有关在甲午海战中,翁氏家族中有多人战死的记载还是有一些,而这些死者多是翁守谦的同胞兄弟。即将寿终正寝的满清王朝,在外忧内患中束手无策,而渴望为朝廷效力的满清人和汉族人,大多心灰意冷,以各种方式寻找“前途”,有的自杀,有的隐居,有的不知所踪。翁守谦属于归隐那一类型的满清官员,他于一八九五年在武昌购置了房产,即现在的昙华林七十五号,便是他当年的住宅。住宅为二层砖木结构,据说现在游客看到的宅邸,与当初还是有不小的差别的。这座私人宅邸,在翁守谦的眼中,跟僧人眼中的寺庙是一样的。翁守谦虽然没有剃度,遁迹空门,终日与青灯黄卷为伴,但也潜心钻研佛教典籍,实际上也是与现实世界断了诸多联系,区别仅仅是在形式上。不难揣测翁老先生终老武汉昙华林的意图,经历过满清末期耻辱,实际上也就是国破家亡的人,大抵是冷了心肠,看透了朝廷的嘴脸,再也没有心思为其卖命,在滚滚红尘和争名夺利中委屈自己,因而走了“极端”,寻得一方好地好水,让心灵宁静下来,与佛结了缘,就再也不想回到尘世,做一个苟且偷生的热闹却无能之人了。
走出大大小小高高低低形形色色的西式或中西结合的建筑,来到缓慢如老妪漫步的昙华林街面上,呼吸几口下午新鲜的空气,看看身边来来往往的各种年龄却无一相识的人,喝几口冰镇饮料,再看看夹杂在发旧的建筑之间的各色小模样且精致精美无比的房屋,便慢慢回归到了现实,方才想起在来昙华林之前,在某宣传片中记住的几句话,其意思就是这里是文青的天地,属于小清新们,有咖啡和绿茶组成的当代中西方休闲板式,有新一代的归隐者,有浪迹天涯后短暂栖息于此的流浪者、诗人、歌者、孤独者或无数无名无份却怀揣着理想和梦的人。
热干面在某本地小青年办的休闲餐厅里被重新更改和定位,属于新新人类的消费美食,而老武汉们的热干面,大抵不乐意进入昙华林,即使来了,新新人类们估计也不给面子的。我不喜欢热干面,因为宜宾的燃面在“干燥热辣”的面食艺术里已经占得一席,而我可是在燃面的氛围中走完了青春之路的。但我又实在绕不开热干面,在所谓的有年轻人改造过的热干面中寻找新的武汉味道和昙华林之魅。但我品尝到的还是老武汉的味道,年轻人的噱头大抵也只是噱头,骨子里哪能脱得开老武汉的风韵?但年轻人喜欢,因为那些洋溢着青春风采的餐桌上,即使是一只可以充当古董的碗,也是年轻人心目中的青春器皿,不装历史,而是装青春,爱情或者寂寞。
在一面有意整饬得带有强烈艺术特色的青砖墙面上,写满了由各地来的游客,尤其是年轻游客用彩色粉笔书写的文字,有人生感言,旅行体验,有对孤独的感悟,对寂寞的留恋,有婚姻启事,自然就有粗俗中见率直、浪漫中见真情的性爱导语,当然,也不乏“某某到此一游”的词句,但在这里,却没有丝毫破坏旅游环境的嫌疑。在这些活乱乱眼扎扎的文字中,最为醒目的还是主人用现代技术贴在上面的文字,比如:“我愿做时光中的一只老害虫,赤脚漫步古街的石板路,尝尽舌尖上的水,寄给世界的情书……”于是,在这句文字四周,便写满了痴情者的文字,这些难看或好看的文字,将他们的内心所思所想,包括爱恨,通过时间或只属于昙华林的某种意会寄走,究竟要寄到哪里,他们并不在意,也不愿意说清楚,只要寄走了,就是了。诗意的心灵必定依附于诗意的世界,但这样的世界只能漂游在朦胧、缱绻的梦中。不愿意醒来的,除了年轻人,也有像我这样的中年人,当然,还有我亲眼看到的一两个老者,他们并没被吝啬而残忍的时间击垮,没有被世人冰冷而嘲笑的眼神击穿,他们也来到了昙华林,做了伴侣的“老害虫”,一起啃吃时光,一起行吟在诗意无边的昙华林。爱情不是活在强大的物质里,而是活在感觉和意会之中,当那些感觉和意会上升到诗意的高度,就成了深刻的抽象,也就成了伟大而恒久的美。
在这次旅行最后的那点时间里,我在各色装饰新潮、充满了浪漫和人文气息的咖啡馆、酒吧中进出,而那些位于巷道深处的精致、优雅、恬静、唯美,却又不失人间烟火味的小酒馆小咖吧,更是让我着迷,一次次坠入诗意和恬静之中。傍晚悄悄来临,昙华林慢慢安静下来,游客纷纷离去,白昼不轻不重的喧闹,被昙华林之外马路上奔驰的车辆喇叭声取代。但这越发衬托出昙华林的清静和悠远。街道两边的古老建筑由于大多没有开放,便没有灯光,迅速坠入初夜的灰暗之中,被黑暗一口吞噬。但对于大大小小,装饰得极富艺术气息和个性色彩的,属于文艺青年或崇尚雅趣与时尚的年轻商贩来说,黑暗是伪命题。此刻的时间正好,或者刚刚开始。优雅地摆放在各色酒馆、书店和小商铺门口的精美桌椅,不管是中式的典雅精致,还是西式的厚重优雅,不管能不能等到它们一天一星期乃至一生都在等待的那个人那些人,它们都无视时间的移动,光影的转换。只有感觉在挪移,每间精心设计的屋子里那些干净明亮的器皿,以及由器皿和人共同营造的氛围,才是他们和它们心仪的内涵,从而成为属于他们的生存哲学和时间观念,从而在时间的最深处坐着,享受美食带来的快乐,或冷静地思索,在思索中直视所有倏忽即逝的人事,让思索具有所有物质元素根本上不可与之媲美的快感,并长时间沉醉于其中。是的,无论是古老的建筑物,还是新潮的居室和居室的主人们,在早亮的灯火与内心的风景相辉映的那一刻,他们就获得了存在,在无数个顷刻间成为诗、音乐、孤独和历史。不到一点五千米长的昙华林,描摹抒写起来太长,对于一个下午孤独的旅行来说又太短,但这正是它的价值和魅力所在。
中国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建筑的历史。青砖黑瓦,飞檐翘角,雕梁斗拱,深深庭院,沾满了血迹、每块石头都是骸骨的长城与诸多伟大的水利工程等,无不是历史最为直接的承载。但音乐是用旋律音符等元素组建起来的悠扬的建筑,美术是用线条、块面、色彩等元素组成的凝固但色彩丰富的建筑,戏剧影视是以舞台、道具、灯光和蒙太奇组成的古代与现代色彩都极其浓郁的建筑,舞蹈是用肉体、服装和对生存乃至生命的有感而发组成的灵与肉的建筑。汉字,在我看来远胜四大发明的汉字,每一个都是一座座精美绝伦的建筑物,而且赋予建筑物平上去入的声调和无数深奥而又极富民族心性的深刻含义。还有什么能比像汉字这样古老又常新的建筑,将华夏文明和民族性格完美地融进其一笔一划一招一式一心一意和卓越的美学意义中,从而让我们冷静,庄严,却又不失浪漫风情,在古往今来和中西携手中,尽情徜徉,自由自在呢?而通过汉字、庭院、嘉木、坚卓的意志和深远的意会带来的感动和吟咏,能不能让后来者获得宁静、达观和美呢?
这一切都在昙华林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呈现,我们执意前来和带着淡淡的忧郁离去,都不能填补或损害其一分一毫。